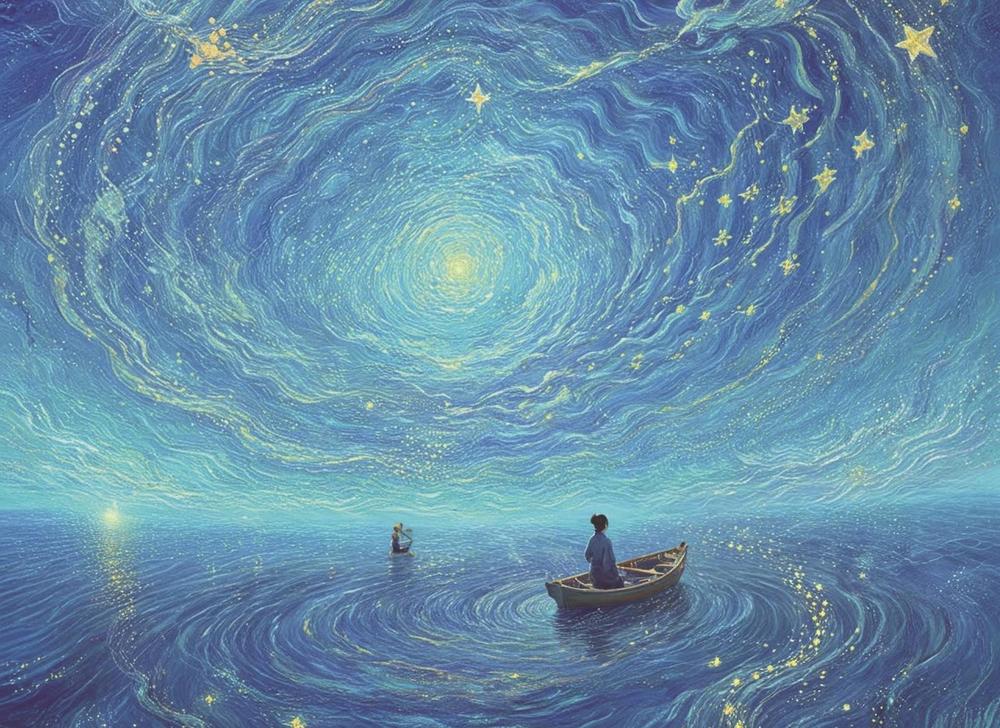□ 韩进勇
跟杨海光老师最初的接触是1986年春天或者夏天。那时候我在县政府办公室综合组(科)工作,我和另一位同事的办公室紧挨着秘书组(科)。我俩那屋没有电话,但秘书组的电话却十分繁忙,电话铃声可谓不绝于耳。秘书组房间的门一天到晚从来不关,我们的办公室除了冬天也经常开着门,年轻人耳朵好使,接打电话的人声音又比较大,隔着房间也能听得清楚。有一次我听到接电话的人这样说道:林森?没有啊。我们办公室没有姓林的啊。写稿子的?我急忙跑过去,抢了那人的电话听筒,向电话那头的人说,我是那稿子的作者,笔名林森。打电话的那人就是杨海光老师。声音洪亮,态度热情,欣喜情绪的气息仿佛从听筒里都能感到扑面而来。
那是我大学毕业的第四年,也是从市区调县的第二年,虽在机关上班,但对本职工作投入的热情远远低于自己的爱好——文学创作。我是个理工男,文科的知识非常缺乏,初入社会,经历阅历又都很少,写出东西来很是幼稚。屡屡投稿,屡屡遭拒,苦闷忧郁的心情无法表达,无人倾诉。然而,文学的吸引力对我是如此之强,时时刻刻心心念念的是文学作品,日夜沉醉在文学世界里。在不太轻松的本职工作的间隙悄悄地或者说偷偷摸摸地看文学书籍,学习文学写作。因为是“地下工作”,单位里也就很少有人知道我写作的事情了。与我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县内文坛的喜人形势。创作群体庞大,创作势头强劲,创作成就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被文坛称作“滦南文学现象”,有人写了《滦南多俊才》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那个时代真可谓滦南文学的春天啊。而文学大咖,县内文坛领袖就在我的身边,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滦南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冯学行。先生当时是全国有名的杂文家,笔名石飞、史非,几乎每月都有大作刊登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而且大都是头条的位置。后来出版了《夜垦集》,获得了首届“河北文艺振兴奖”。先生也担任过首任县文联主席。在他的带领下,域内形成了杂文创作群体,著名的石飞、兰楠、汪金友“杂文三杰”便是其中的核心和灵魂。与此同时,小说作家肖波、杨海光、刘振广创作风头正盛,剧作家谷景峰、谷顺祥的作品引人注目。此外还有一位既是圈里又是圈外的文人,时任《唐山劳动日报》驻县记者的张哲明。他后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哲明兄的文学评论一起步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如果说当年冯学行先生是滦南文坛的一面旗帜,那么张哲明则是从滦南这块土地上横空出世的一颗文学新星,更准确地说是文学评论界的“一匹黑马”。他的一篇发表在《作品与争鸣》上的文章,真就符合了刊物的宗旨,一时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他给石飞写的《石落长河有回声》评论文章曾在文坛引出了一桩美谈。1989年冯先生的《夜垦集》出版,请《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刘甲为之作序。刘先生却对张哲明的那篇文章表达了欣赏和佩服,大有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遂把那篇评论也做了序言。这是对当时三十岁刚出头作者的赞赏,我想也是对当时滦南文学实力的肯定。家乡文学创作蔚然成风,惊喜不断,这让我备受鼓舞,一个文学青年心头的创作热情像野火遇上春风更加旺盛。对县内文坛有欲入楼台之心,却因为没有“敲门砖”望而却步。在多次遭到县以上刊物退稿或“无应答”之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一篇题目是《夏夜,在故乡那棵老槐树下》的散文投给了《滦南文艺》。单位和《滦南文艺》编辑部所在的文化馆虽只有一里之遥,我却趁街头行人稀少的时间,紧张而又快速地投进了路边的邮筒。
杨海光老师打电话正是收到那篇稿件之后,按着注明单位寻找作者的。我写东西是瞒着周围人的,用的林森那个笔名就更无人知晓了。文史知识严重缺乏的我,根本不知道林森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位大人物,后来这个笔名就不敢再用了。老师那样热情,那样友善,并诚恳邀请见面,令我十分兴奋。其实,在当时滦南的文人中,杨海光、朱永远是我知道名字最早的两位作家,可谓未识其面,先读其文。大三那年,我在学校图书馆从《河北文学》期刊上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闪光的算珠》,作品的主人公是我国著名的珠算专家、我的高中老师朱永茂,作者是杨海光和朱永远,而朱永远则是我们朱老师的亲弟弟。从那时起,我便记住了这两位作家,他们的名字也和他们所描绘赞美的算珠一样,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到县城工作后,也听说了两位的工作单位,但由于前面讲过的顾虑,虽有心求见,却总是想而却步。老师的邀请让我顾虑全消,不几日便前往拜见。文化馆在城中皋上西坡也就是现在成兆才大戏院的位置,那是由两层楼四面合围起来的院落,多家单位共同使用。评剧团、歌舞团、图书馆、文联、文化馆都在其中。那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地方,从早到晚,锣鼓时时响起,琴笛之音绵绵不绝,更有咿咿呀呀的唱念和充满活力的歌声贯穿始终,嘈杂而兴旺。作家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了他们的高峰之作。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是一个文化高地,更是文学高地。在里边办公的有肖波、杨海光、谷景峰、谷顺祥等作家。杨海光和“二谷”老师还吃住在此。冯先生隔三差五光临,朱永远老师是常客,好像从县财政局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王守谦老先生也时有惠顾。不喝酒、不打牌,会抽烟的则彼此点烟对火,那满屋子的烟气呛人又让人感到亲切。他们畅谈文学、交流心得、讨论问题、互通见闻又争辩观点。杨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在北面靠东的位置,夫人也和他一起吃住在此。第一感觉是杨老师脸上的光彩,高颧骨、大脸庞、大眼睛,和他的名字一样,我看到老师满面放光。老师是个大个子,在狭小的屋子里更显得身材魁梧。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灿烂的笑容和朗朗的笑声。是那种绽放度很大的笑容,那种轰鸣的、震动你情绪的笑声。后来相见,无论何时何地,老师总是那样的“初容”“初声”。那次接触,彼此一见如故,相识恨晚。老师的直率、坦诚,是在作家中很少见到的。鼓励指导,意见中肯,态度鲜明。那次相见之后,老师让我有了文学上的自信心,接连给了他几篇稿子,都被采纳。其中有一篇《关于京腔女大学生日记》的短篇小说占了刊物很大版面。经老师推荐,我的散文还获得了县里举办的文学奖。老师不仅指导发表我的作品,还把他刚写或正在写的作品拿出来,让我提意见。我呢,就真不知深浅地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老师竟然诚恳地接受。记得我们还对作品里的情节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角度产生了辩论。老师不恼,却以此为乐。那几年,到老师那里坐坐是桩乐事,也总有收获。
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变化,后来与老师接触就没有当初那么多了,但偶有相见,老师总是笑容满面,也总是对我反反复复地嘱咐“写东西得坚持啊,没扔了吧?”“还写呢吗?千万不能扔啊!”当我再次从县外调回家乡工作的时候,老师已经退休,回归故里,长期生活在渤海岸边的镇子——柳赞。虽然前几年这个镇划入相邻行政区域,但先生几乎一生都是滦南人,“滦南情结”始终未变。他不仅自己热情创作,还指导和带领年轻的作者书写滦南人物、滦南故事。我们的感情也一如既往。12年前,县作家协会换届之后,他是我们唯一的“县外”顾问。老师有严重的心脏病,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没啥事儿,就是想唠唠嗑,我知道老师是想我想念朋友了,于是约了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高会臣一同看望老人。老人甚得安慰,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老师提出一个计划,说等他把房子好好装修一下,办一个他文学创作生涯的纪念活动。我们当然赞成并表示全力支持。去年年底,由县作协提议,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县作协给六位老作家颁发了“滦南县文学创作荣誉奖”,杨老师是当然的获奖者。考虑到老师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路途又远,我们打电话说过些日子把奖牌送到家中,老师表示非常感谢。那段时间我市区县城两头跑着忙家里的事情,上门送奖牌的事儿就耽搁了一些时日。老师“拿奖”心情迫切,要委托文友给他捎过去。我得知情况后,抓紧和文联张伟主席、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高会臣专程到家里为老师颁赠了奖牌。老师在家乡威望高,影响大。那天,村里四任书记全部到场,其中包括八十多岁的老书记,年轻的时候和身为大队会计的杨老师是非常好的搭档和朋友。老师的作品曾多次获奖,但他对这个奖牌格外看重,或许家乡的肯定是最根本的肯定,乡亲们的祝贺最让人欣慰。授奖、拍照、录视频,老师开心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洋溢着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神情,根本看不出老人家有病在身。他儿子、孙女也参与见证了老人的“高光时刻”。我们还确定了“杨海光文学创作六十五周年座谈会”大体的时间和主要内容。这对他本人意义重大,对滦南文坛来说也是一项重要活动。然而,离老人家盼望的时间一天近似一天的时候,老师却突然离世,驾鹤西行。人已去,愿未了,逝者抱憾,参与策划活动的人也叹息不已。
这几天,我除了回忆和老师的交往之外,也翻阅了老师的作品。在老师数以百万字计的作品中,大海风云和渔民生活是他主要的主题和最多的题材。从六十年代初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渔民恨》,到2015年的长篇小说《船》,几十年间老师创作了大量“冒着海腥气”的作品。《渔港风波》《鱼水情深》《风流的海》《海嫂》《乘风破浪》《碧海新歌》《渔乡新曲》《大海探宝》……不用说里边的故事和人物,光看这些名字,眼前好像就汹涌起一片汪洋大海。再想到他的性格,就可以知道,老师一生爱海恋海写海,内心始终奔涌着大海。他是大海之子,是渔民的作家。他的一生总是张开怀抱拥抱大海,也感染和传递了大海的激情。晚年选择回到海边,守着大海,生活在渔民中间,不仅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而且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承担。他是全村乃至相邻村庄渔民的代言人、笔杆子。乡亲们凡是动笔写字的事儿,都是找到他家中,他总是有求必应。去年为村里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写就了一本《柳赞二村村史》,不仅为家乡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填补了附近一带沿海村镇的史志空白,用生命最后的时光完成了家乡赋予他的使命。从海边走向世界,从渔家走向文坛,他用生命的余晖回报乡里,回报大海,把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捧给了广阔深厚的大海,这是乡亲和大海的慰藉,也是他为自己画上的圆满的人生句号。和乡亲们一样,老师的坟墓也在海边,他的魂骨朝夕相伴大海的波涛。突然再次品味老师的名字,杨海光——大海之光。多么贴切!老师,从此,我再看到波涛汹涌的大海,定会想起您响亮的名字,想到您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