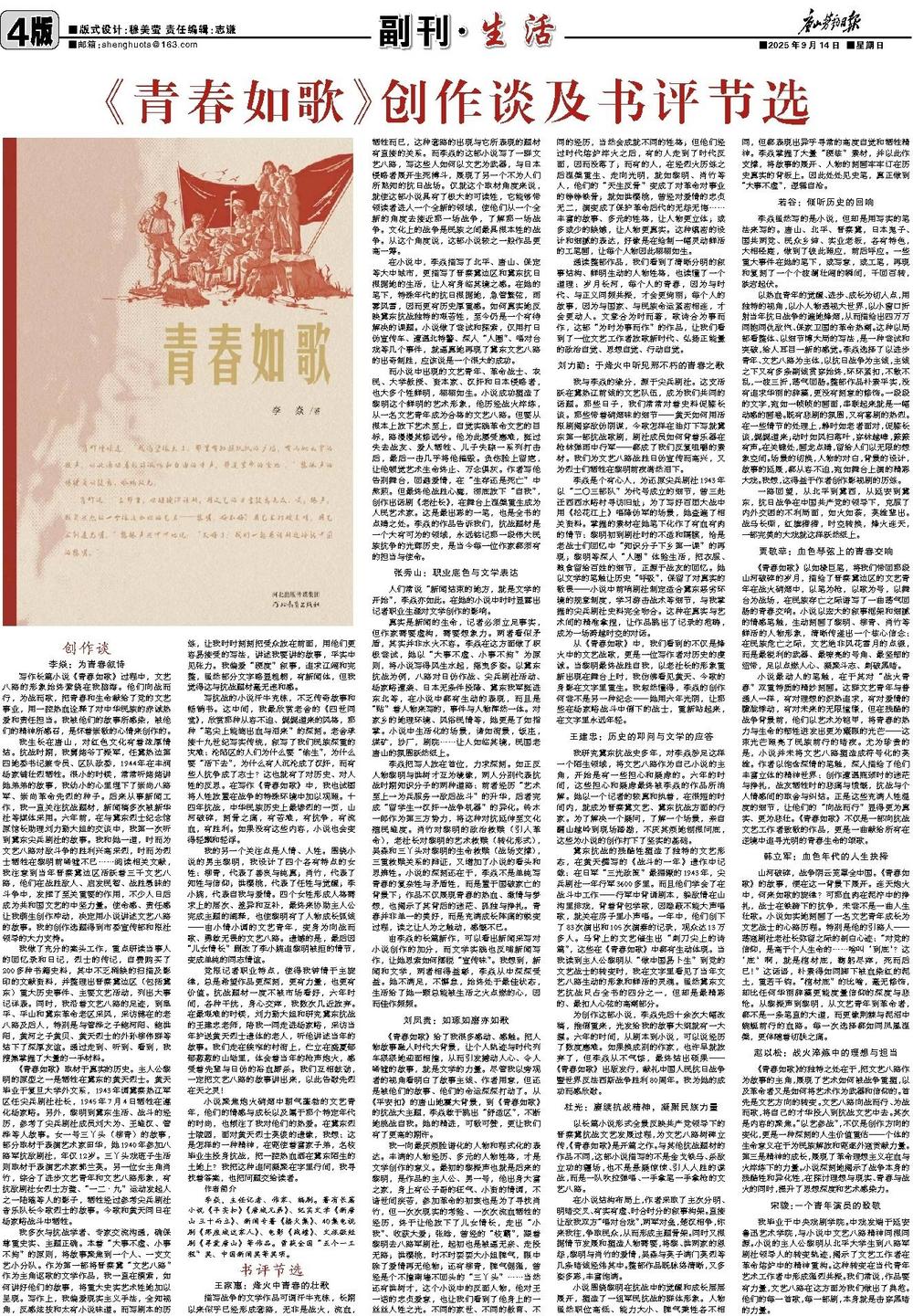创作谈
李焱:为青春叙诗
写作长篇小说《青春如歌》过程中,文艺八路的形象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他们向战而行,为战而歌,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用一腔热血诠释了对中华民族的赤诚热爱和责任担当。我被他们的故事所感染,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创作的。
我生长在唐山,对红色文化有着浓厚情结。抗战时期,我舅姥爷丁振军,任冀热边第四地委书记兼专员、区队政委,1944年在丰润杨家铺壮烈牺牲。很小的时候,常常听姥姥讲她弟弟的故事,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崇尚八路军、崇尚革命先烈的种子。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我一直关注抗战题材,新闻稿多次被新华社等媒体采用。六年前,在与冀东烈士纪念馆原馆长助理刘力勤大姐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冀东尖兵剧社的故事。我和她一道,时而为文艺八路对敌斗争的胜利兴高采烈,时而为烈士牺牲在黎明前唏嘘不已……阅读相关文献,我注意到当年晋察冀边区活跃着三千文艺八路,他们在战胜敌人、启发民智、战胜愚昧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人日后成为共和国文艺的中坚力量。使命感、责任感让我萌生创作冲动,决定用小说讲述文艺八路的故事。我的创作选题得到市委宣传部和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
我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重点研读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日记,烈士的传记,自费购买了200多种书籍史料,其中不乏稀缺的扫描及影印的文献资料,并整理出晋察冀边区(包括冀东)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文艺活动,列出大事记详表。同时,我沿着文艺八路的足迹,到阜平、平山和冀东革命老区采风,采访健在的老八路及后人,特别是与管桦之子鲍河阳、鲍洪阳,黄河之子黄贝、黄天烈士的外孙柳伟群等结下了深厚友谊。通过走到、听到、看到,我搜集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青春如歌》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主人公黎明的原型之一是牺牲在冀东的黄天烈士。黄天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43年调冀察热辽军区任尖兵剧社社长,1945年7月4日牺牲在遵化杨家峪。另外,黎明到冀东生活、战斗的经历,参考了尖兵剧社成员刘大为、王维汉、管桦等人故事。女一号三丫头(柳青)的故事,部分取材于表演艺术家田华,她1940年参加八路军抗敌剧社,年仅12岁。三丫头戏班子生活则取材于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另一位女主角肖竹,综合了进步文艺青年和文艺八路形象,有抗敌剧社女烈士方璧、“一二·九”运动发起人之一陆璀等人的影子,牺牲经过参考尖兵剧社音乐队长今歌烈士的故事。今歌和黄天同日在杨家峪战斗中牺牲。
我多次与抗战学者、专家交流沟通,确保尊重史实、主题正确。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将故事聚焦到一个人、一支文艺小分队。作为第一部将晋察冀“文艺八路”作为主角讴歌的文学作品,我一直在摸索,如何讲好他们的故事,将重大史实艺术性地加以呈现。写作上,我偏爱现实主义手法,全知视角,反感炫技和太有小说味道。而写剧本的历练,让我时时刻刻把受众放在前面,用他们更容易接受的写法,讲述我要讲的故事,平实中见张力。我偏爱“硬度”叙事,追求辽阔和完整,虽然部分文字略显粗粝,有新闻体,但我觉得这与抗战题材毫无违和感。
写抗战的小说汗牛充栋,不乏传奇故事和畅销书。这中间,我最欣赏老舍的《四世同堂》,欣赏那种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风格,那种“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深刻。老舍承接十九世纪写实传统,叙写了我们民族深重的灾难:沦陷区的人们为什么要“偷生”,为什么要“活下去”,为什么有人沉沦成了汉奸,而有些人抗争成了志士?这也就有了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在写作《青春如歌》中,我也试图将人性放置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加以观照。十四年抗战,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烈的一页,山河破碎,刻骨之痛,有苦难,有抗争,有流血,有胜利。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小说也会变得轻飘和轻浮。
我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情、人性。围绕小说的男主黎明,我设计了四个各有特点的女性:柳青,代表了善良与纯真;肖竹,代表了知性与信仰;洪樱桃,代表了任性与觉醒;李小婉,代表自我与爱情。四个女性形成人格需求上的层次、差异和互补,最终来协助主人公完成主题的阐释,也使黎明有了人物成长弧线——由小情小调的文艺青年,变身为向战而歌、勇敢无畏的文艺八路。遗憾的是,最后因“儿女情长”删改了李小婉追黎明被拒的情节,变成单纯的同志情谊。
党报记者职业特点,使得我钟情于主旋律,总是希望作品更深刻,更有力量,也更有价值。抗战题材一度不被市场看好,六年时间,各种干扰,身心交瘁,我数次几近放弃。在最艰难的时候,刘力勤大姐和研究冀东抗战的王建忠老师,陪我一同走进杨家峪,采访当年护送黄天烈士遗体的老人,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我们走在狭窄的村街上,伫立在盛夏郁郁葱葱的山坳里,体会着当年的枪声炮火,感受着先辈与日伪的浴血厮杀。我们互相鼓劲,一定把文艺八路的故事讲出来,以此告慰先烈在天之灵!
小说聚焦炮火硝烟中朝气蓬勃的文艺青年,他们的情感与成长以及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时尚,也倾注了我对他们的热爱。在冀东烈士陵园,面对黄天烈士英俊的遗像,我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在驱使着富家子弟,名校毕业生投身抗战,把一腔热血洒在冀东陌生的土地上?我把这种追问凝聚在字里行间,我寻找着答案,也把问题交给读者。
作者简介
李焱,主任记者、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平安扣》《唐城兄弟》、纪实文学《新唐山 三十而立》、新闻专著《播火集》、40集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电影《战蝗》、文旅微短剧《寻爱唐山》等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等奖项。
书评节选
王家惠:烽火中青春的壮歌
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长期以来似乎已经形成套路,无非是战火,流血,牺牲而已,这种套路的出现与它所表现的题材有直接的关系。而李焱的这部小说写了一群文艺八路,写这些人如何以文艺为武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生死搏斗,展现了另一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抗日战场。仅就这个取材角度来说,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极大的可读性,它能够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使他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接近那一场战争,了解那一场战争。文化上的战争是民族之间最具根本性的战争。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较之一般作品更高一筹。
在小说中,李焱描写了北平、唐山、保定等大中城市,更描写了晋察冀边区和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在她的笔下,特殊年代的抗日根据地,急管繁弦,雨雾风雪,因而更有历史厚重感。如何真实地反映冀东抗战独特的艰苦性,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小说做了尝试和探索,仅用打日伪宣传车、遭遇北特警、深入“人圈”、唱对台戏等几个事件,就逼真地再现了冀东文艺八路的出奇制胜,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而小说中出现的文艺青年、革命战士、农民、大学教授、资本家、汉奸和日本侵略者,也大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小说成功塑造了黎明这个鲜明的艺术形象,他历经战火淬炼,从一名文艺青年成为合格的文艺八路。但要从根本上放下艺术至上,自觉实践革命文艺的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他为此屡受磨难,挺过失去战友、爱人牺牲、儿子失踪一系列打击后,最后一击几乎将他摧毁。负伤脸上留疤,让他顿觉艺术生命终止、万念俱灰。作者写他告别舞台,回避爱情,在“生存还是死亡”中熬煎。但最终他战胜心魔,彻底放下“自我”,创作出话剧《老社长》,在舞台上涅槃重生成为人民艺术家。这是最出彩的一笔,也是全书的点睛之处。李焱的作品告诉我们,抗战题材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永远铭记那一段伟大民族抗争的光辉历史,是当今每一位作家都须有的担当与使命。
张秀山:职业底色与文学表达
人们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的开始”,李焱亦如此。在她的小说中时时显露出记者职业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必须立足事实,但作家需要虚构,需要想象力。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非水火不容。李焱在这方面做了积极尝试,她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将小说写得风生水起,摇曳多姿。以冀东抗战为例,八路对日伪作战、尖兵剧社活动、杨家峪遭袭、日本无条件投降、冀东我军挺进东北等,在小说中都有生动的表现,而且是“贴”着人物来写的,事件与人物浑然一体。对家乡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等,她更是了如指掌。小说中生活化的场景,诸如街景,饭庄,煤矿,纱厂,剧院……让人如临其境,民国老唐山的氛围跃然纸上。
李焱把写人放在首位,力求深刻。如正反人物黎明与洪树才互为镜像,两人分别代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道路:前者经历“艺术至上→为兵服务→敌后战斗”的升华,后者完成“留学生→汉奸→战争机器”的异化。铃木一郎作为第三方势力,将这种对抗延伸至文化殖民维度。肖竹对黎明的政治救赎(引入革命),老社长对黎明的艺术救赎(转化形式),吴森和三丫头对黎明的生命救赎(战场支撑),三重救赎关系的辩证,又增加了小说的看头和思辨性。小说的深刻还在于,李焱不是单纯写青春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是置于国破家亡的背景下;作品不仅展现青春的热血、激情与梦想,也揭示了其背后的迷茫、孤独与挣扎。青春并非单一的美好,而是充满成长阵痛的蜕变过程,读之让人为之触动,感慨不已。
由李焱的长篇新作,可以看出新闻采写对小说创作的加分,而文学实践也反哺新闻写作,让她思索如何摆脱“宣传味”。我想到,新闻和文学,两者相得益彰,李焱从中深深受益。她不满足,不懈怠,始终处于最佳状态,生活给了她一颗总能被生活之火点燃的心,因而佳作频频。
刘凤贵:如琢如磨亦如歌
《青春如歌》给了我很多感动、感触。把人物故事融入时代大背景,让个人轨迹与时代列车狠狠地迎面相撞,从而引发撼动人心、令人唏嘘的故事,就是文学的力量。尽管我以旁观者的视角看明白了故事主线、作者用意,但还是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命运深深打动了。从《平安扣》的唐山地震大背景,到《青春如歌》的抗战大主题,李焱敢于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自我。她的精进,可敬可赞,更让我们有了更高的期许。
我一向最厌烦脸谱化的人物和程式化的表达。丰满的人物经历、多元的人物性格,才是文学创作的意义。最初的黎振声也就是后来的黎明,是作品的主人公、男一号,他出身大富之家,身上有公子哥的狂气、小资的情调,不谙世间疾苦,参加革命的初衷也是为了寻找肖竹,但一次次现实的考验、一次次流血牺牲的经历,终于让他放下了儿女情长,走出“小我”、收获大爱;张晗,曾经的“校霸”,跟着黎明去八路军剧社,起初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洪樱桃,时不时耍耍大小姐脾气,眼中除了爱情再无他物;还有柳青,脾气倔强,曾经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三丫头”……当然还有洪树才,这个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他对王一诺的忠贞爱意,也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一丝丝人性之光。不同的家世、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经历,当然会成就不同的性格;但他们经过时代熔炉淬火之后,有的人走到了时代反面,因而没落了;而有的人,在经烈火历练之后涅槃重生、走向光明,就如黎明、肖竹等人,他们的“天生反骨”变成了对革命对事业的铮铮铁骨;就如洪樱桃,曾经对爱情的忠贞无二,演变成了保护革命后代的无怨无悔……丰富的故事、多元的性格,让人物更立体;或多或少的缺憾,让人物更真实。这种缜密的设计和细腻的表达,好像是在绘制一幅灵动鲜活的工笔画,让每个人物因此栩栩如生。
通读整部作品,我们看到了清晰分明的叙事结构、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也读懂了一个道理:岁月长河,每个人的青春,因为与时代、与正义同频共振,才会更绚丽;每个人的故事,因为与国家、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才会更动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部“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文艺工作者放歌新时代、弘扬正能量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刘力勤:于烽火中听见那不朽的青春之歌
我与李焱的缘分,源于尖兵剧社。这支活跃在冀热辽前线的文艺队伍,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那些日子,我们常常对着史料促膝长谈。那些带着硝烟味的细节——黄天如何用活报剧揭穿敌伪阴谋,今歌怎样在油灯下写就冀东第一部抗战歌剧,剧社成员如何背着乐器在枪林弹雨中行军——都成了我们反复咀嚼的素材。我们为文艺八路战胜日伪宣传而高兴,又为烈士们牺牲在黎明前夜潸然泪下。
李焱是个有心人,为还原尖兵剧社1943年以“二〇三部队”为代号成立的细节,曾三赴迁西西水峪村寻访旧址;为了写好百团大战中用《松花江上》唱降伪军的场景,她查遍了相关资料。掌握的素材在她笔下化作了有血有肉的情节:黎明初到剧社时的不适和隔膜,恰是老战士们回忆中“知识分子下乡第一课”的再现;黎明等深入“人圈”体验生活,把衣服、粮食留给百姓的细节,正源于战友的回忆。她以文学的笔触让历史“呼吸”,保留了对真实的敬畏——小说中前哨剧社制定适合冀东恶劣环境的规章制度,学习游击战术等细节,与我掌握的尖兵剧社史料完全吻合。这种在真实与艺术间的精准拿捏,让作品跳出了记录的范畴,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从《青春如歌》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烽火中的文艺战歌,更是一位写作者对历史的虔诚。当黎明最终战胜自我,以老社长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时,我仿佛看见黄天、今歌的身影在文字里重生。我忽然懂得,李焱的创作何尝不是另一种纪念——她用六年光阴,让那些在杨家峪战斗中倒下的战士,重新站起来,在文字里永远年轻。
王建忠:历史的叩问与文学的应答
我研究冀东抗战史多年,对李焱涉足这样一个陌生领域,将文艺八路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角,开始是有一些担心和疑虑的。六年的时间,这些担心和疑虑最终被李焱的作品所消解。她以一个记者的较真和执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晋察冀文艺、冀东抗战方面的行家。为了解决一个疑问,了解一个场景,亲自翻山越岭到现场踏勘,不厌其烦地刨根问底,这些为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冀东抗战的残酷性塑造了独特的文艺形态,在黄天撰写的《战斗的一年》遗作中记载:在日军“三光政策”最猖獗的1943年,尖兵剧社一年行军3600多里。而且他们学会了在战斗中工作——行军中背诵剧本,躲敌情在山沟里排戏,背着背包学歌,因隐蔽不能大声唱歌,就关在房子里小声唱。一年中,他们创下了83次演出和105次演奏的记录,观众达13万多人。马背上的文艺催生出“刺刀尖上的诗篇”,这些在《青春如歌》中都有生动体现。当我读到主人公黎明从“做中国易卜生”到党的文艺战士的转变时,我在文字里看见了当年文艺八路生动的形象和鲜活的灵魂。虽然冀东文艺抗战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但却是最精彩的、最扣人心弦的高潮部分。
为创作这部小说,李焱先后十余次大幅改稿,推倒重来,光发给我的故事大纲就有一大摞。六年的时间,从剧本到小说,可以说经历了数度磨难。如果换成别的作家,也许早就放弃了,但李焱从不气馁,最终结出硕果——《青春如歌》出版发行,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为她的成功而感欣慰。
杜光:赓续抗战精神,凝聚民族力量
以长篇小说形式全景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战文艺发展过程,为文艺八路树碑立传,《青春如歌》是开篇之作。与其他抗战题材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描写的不是金戈铁马、杀敌立功的疆场,也不是悬疑惊悚、引人入胜的谍战,而是一队吹拉弹唱、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文艺八路。
在小说结构布局上,作者采取了主次分明、明暗交叉、有实有虚、时合时分的叙事构架。直接让敌我双方“唱对台戏”,两军对垒,楚汉相争,你来我往,争取民众,从而形成主题骨架。同时又根据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需要,将黎、洪两家的恩怨,黎明与肖竹的爱情,吴森与英子满门英烈等几条暗线经纬其中。整部作品既脉络清晰,又多姿多彩,丰富饱满。
小说围绕黎明在抗战中的觉醒和成长层层展开,塑造了一组军民抗战的群体形象。人物虽然职位高低、能力大小、脾气秉性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自觉和牺牲精神。李焱掌握了大量“硬核”素材,并以此作支撑,将故事的展开、人物的刻画牢牢订在历史真实的背板上。因此处处见史笔,真正做到“大事不虚”,逻辑自洽。
若谷:倾听历史的回响
李焱虽然写的是小说,但却是用写实的笔法来写的。唐山、北平、晋察冀,日本鬼子、国共两党、民众乡绅、实业老板,各有特色,大相径庭,做到了彼此照应,前后呼应。一些重大事件在她的笔下,或写意,或工笔,再现和复刻了一个个波澜壮阔的瞬间,千回百转,跌宕起伏。
以热血青年的觉醒、进步、成长为切入点,用独特的视角,以小人物透视大世界,以小窗口折射当年抗日战争的遍地烽烟,从而描绘出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革命热潮。这种以局部看整体、以细节博大局的写法,是一种尝试和突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李焱选择了以进步青年、文艺八路为主体,以抗日战争为主线,主线之下又有多条副线贯穿始终,环环紧扣,不散不乱,一波三折,荡气回肠。整部作品朴素平实,没有追求华丽的辞藻,更没有刻意的修饰。一段段的文字,宛如一帧帧的画面,串联起来就是一幅动感的画卷。既有悲剧的氛围,又有喜剧的热烈。在一些情节的处理上,静时如老者面对,促膝长谈,娓娓道来;动时如风扫落叶,穿林越嶂,簌簌有声。在关键处,画龙点睛,留给人们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场景的切换,人物的对白,背景的设计,故事的延展,都从容不迫,宛如舞台上演的精彩大戏。我想,这得益于作者创作影视剧的历练。
一路回望,从北平到冀西,从延安到冀东,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如火如荼,英雄辈出。战马长嘶,红旗猎猎,时空转换,烽火连天,一部完美的大戏就这样跃然纸上。
贾敬苹:血色琴弦上的青春交响
《青春如歌》以如椽巨笔,将我们带回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描绘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青年在战火硝烟中,以笔为枪,以歌为号,以舞台为战场,在民族存亡之际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青春交响。小说以宏大的叙事框架和细腻的情感笔触,生动刻画了黎明、柳青、肖竹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清晰传递出一个核心信念:在民族危亡之际,文艺绝非风花雪月的点缀,而是最锐利的武器、最嘹亮的号角、最坚韧的纽带,足以点燃人心、凝聚斗志、刺破黑暗。
小说最动人的笔触,在于其对“战火青春”双重特质的精妙刻画。这群文艺青年与普通人一样,有对理想的炽热追求,有对爱情的朦胧悸动,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但在残酷的战争背景前,他们以艺术为铠甲,将青春的热力与生命的韧性迸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这束光芒照亮了民族前行的暗夜。尤为珍贵的是,小说并未将文艺八路塑造成符号化的英雄。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深入描绘了他们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创作遭遇瓶颈时的迷茫与挣扎,战友牺牲时的悲痛与愤慨,抗战与个人情感间的取舍与纠结。正是这些充满人性温度的细节,让他们的“向战而行”显得更为真实、更为悲壮。《青春如歌》不仅是一部向抗战文艺工作者致敬的作品,更是一曲献给所有在逆境中追寻光明的青春生命的颂歌。
韩立军:血色年代的人生抉择
山河破碎,战争阴云笼罩全中国。《青春如歌》的故事,便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连天炮火中,何来如歌的旋律?可那血肉在泥泞中的挣扎,战士在铁蹄下的抗争,未尝不是一曲人生壮歌。小说如实地刻画了一名文艺青年成长为文艺战士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引路人——荡寇剧社老社长弥留之际的剖白心迹:“对党的信仰,是高于个人生命的……啥叫‘到底’?这‘底’啊,就是棺材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话语,朴素得如同脚下被血染红的泥土,重若千钧。“棺材底”的比喻,毫无修饰,却比任何华丽辞藻更能度量信仰的深度与悲怆。从黎振声到黎明,从文艺青年到革命者,都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更像荆棘与泥沼中蜿蜒前行的血路。每一次选择都如同凤凰涅槃,更伴随着切肤之痛。
赵以松:战火淬炼中的理想与担当
《青春如歌》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文艺八路作为故事的主角,展现了艺术如何被战争重塑,以及革命者又是如何将艺术作为武器和信仰的。首先是文艺方向的转变。文艺八路向战而行、为战而歌,将自己的才华投入到抗战文艺中去。其次是内容的聚焦。“以艺参战”,不仅是创作方向的变化,更是一种深刻的人生价值重估——个体的生命意义在于为民族解放和驱逐外寇贡献力量。第三是精神的成长,展现了革命理想主义在血与火淬炼下的力量。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异化性,在探讨理想与现实、青春与战火的同时,提升了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宋骏:一个青年演员的致敬
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中戏发端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小说中文艺八路精神同根同源。小说的主人公黎明从北平大学生到八路军剧社领导人的转变轨迹,揭示了文艺工作者在革命熔炉中的精神重构。这种转变在当代青年艺术工作者中形成强烈共振。我们常说,作品要有力量,文艺八路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他们的每一首歌,每一部剧,本身就是击穿黑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