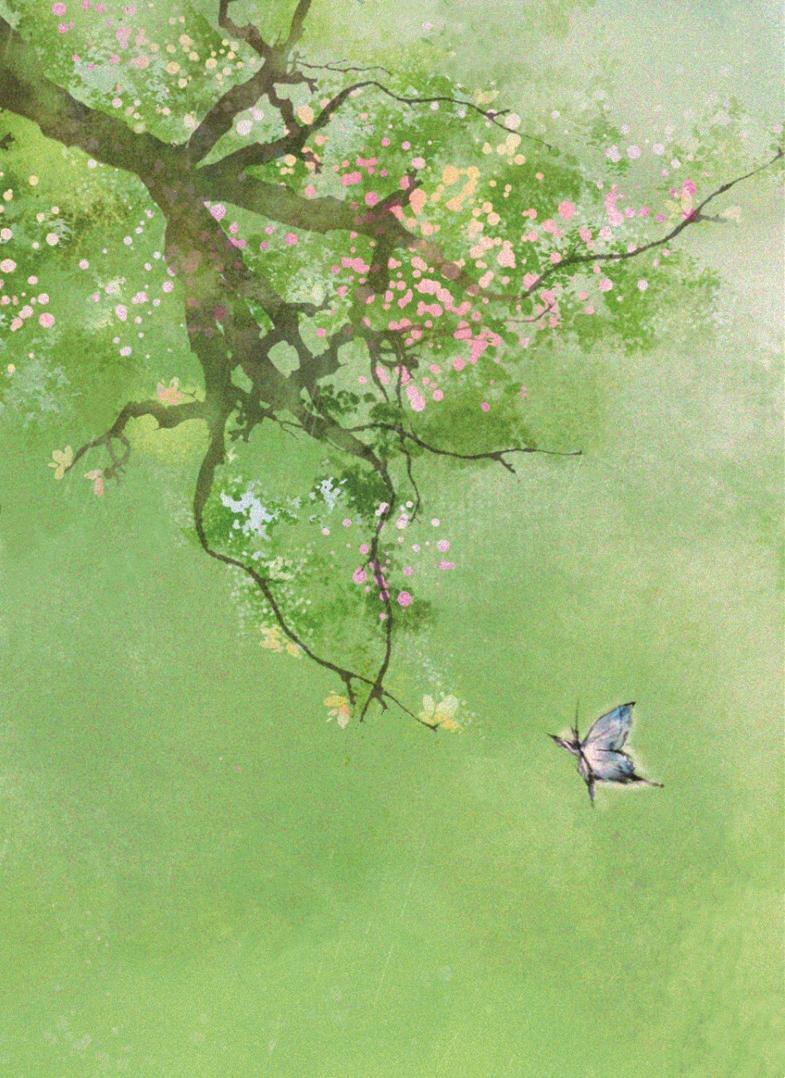桐花万里路
我们不知道她姓什么,只知道她年方十七,是个属兔的女孩。我们也不知道她生得如何,或许她颇有几分姿色,或许她只是“略平头正脸”,作者没有正面描写,我们也不得而知。或许,她也曾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是宝玉眼中“无价的宝珠”,毕竟,她有那样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名字:秋桐。
梧桐是我国最早的著名树种之一。在中国古代,梧桐树可谓是宠儿,从魏晋时期开始,人们就热衷于种植梧桐,此风俗至汉、唐、宋、元、明、清,经久不衰,历代诗文中也都留下了它的足迹。梧桐树型优美挺拔,观赏价值高。人们喜欢它,欣赏它,赋予它美好的寓意。
曹公擅长隐喻,他笔下的人名里也经常暗藏禅机。“秋桐”之名,美得令人过目不忘,只是这名字的所有者却徒有虚名,与这美好背道而驰。但凡知道秋桐的人,怕是都忍不住要套用宝玉的话来吐槽:她哪里配比这树?没的玷污了好名好姓的呢。
金井梧桐秋叶黄
虞世南在赞扬蝉的诗中写道:“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写蝉择良木而栖,赞美蝉的同时,也赞美了梧桐的高洁。可是“品性高洁”之于秋桐,却更像是反讽。
她的出身我们不清楚,作者没有交代她是家生子还是外头买来的。她一出场就是贾赦房里的大丫鬟。贾赦乃荣国府的长房,贾府规矩,服侍过长一辈的奴仆是有些个“体面”的,秋桐想必也有些“体面”。但这所谓“体面”并非是给奴仆本人的,而是源于对其服侍对象的尊重。说到底,奴婢是主子的附属品罢了。做了贾赦房里的丫鬟,秋桐是不幸的:奴婢本就是低人一等,没有自由,更有甚者,她竟然还被贾赦长期霸占着不得婚配,恰应了宝玉行酒令上那句“青春已大守空闺”。贾赦的荒唐无耻,连亲妈都颇有微词:“老爷如今上了年纪,作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没的耽误了人家。”十七岁的秋桐可不就是被贾赦耽误了吗?只不过,秋桐充其量只是个被贾赦“收用”了的大丫鬟罢了,连小老婆都不算,因此处境更为凄惨。
我总觉得,贾母是有悲悯情怀的老人家,也深谙人性。与其说她是对自己这个大儿子有偏见,倒不如说是对贾府门楣的忧虑:那些被大老爷耽误了的女子们会不会不甘寂寞,生了异心,做出有辱门风的丑事来?事实上,那些被贾赦误了芳华的女孩子,确实心怀怨恨,“除了几个知礼有耻的,余者或有与二门上小幺儿们嘲戏的。甚至于与贾琏眉来眼去相偷期的,只惧贾赦之威,未曾到手”。秋桐,恰是其中一个不知礼亦不知耻的。
梧桐昨夜西风急
绝大多数的丫鬟,大了就要由主子做主配小厮,也有被主子格外开恩赏给其父母自行婚配的。此外还有一些出类拔萃的要留给主子做妾,如长一辈的赵姨娘就是贾府家生女儿出身,给贾政做了妾。再如袭人于宝玉,平儿于贾琏,都是通房大丫头,有妾之实,暂无妾之名。只有鸳鸯是贾赦曾经一心要求娶的,邢夫人曾经对鸳鸯亲口承诺,一进门便“开了脸”,直接封作姨娘。只是鸳鸯是个有心胸有眼界的好姑娘,对于做小老婆深恶痛绝,以死抗婚,不肯妥协。
不知道对于鸳鸯抗婚的事秋桐怎么看呢?秋桐不是鸳鸯,在她的认知里,鸳鸯放着现成的姨娘不当,无异于傻子。因此,当被贾赦像个物件一样赠与贾琏时,秋桐终于迎来了她人生的“高光时刻”。什么尊严与人格,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在她那里根本就不存在。
关于尊严,抄检大观园时,我们在晴雯倾倒的箱子里见到过,在鸳鸯抗婚时铰掉的头发里见到过,在梨香院的龄官拒演时看见过,甚至在彩云承认偷盗了玫瑰露时也见到过……她们虽也都是女奴,却以自尊自爱维护了个人尊严,让我们看到了人心的尊贵。与之相比,秋桐毫无尊严,全无心肝,我们不知道她在贾赦房里经历了什么,有怎样的不堪的过往,在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人性的光芒,只看到她极其享受自己的“升迁”飞跃,从贾赦的丫鬟到贾琏的姨娘,她仿佛麻雀一朝飞上了枝头,自己便把自己当成了“凤凰”。
“身为下贱”不是秋桐的错,“心比天高”也无可厚非,但是她不该在抛弃了廉耻之后也丧失了做人最后的尊严与底线。秋桐不以自己与贾赦父子的混乱关系为耻,却将自己出身大老爷房里为荣,甚至自觉高人一等,连凤姐和平儿皆不放在眼里。如此种种,简直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