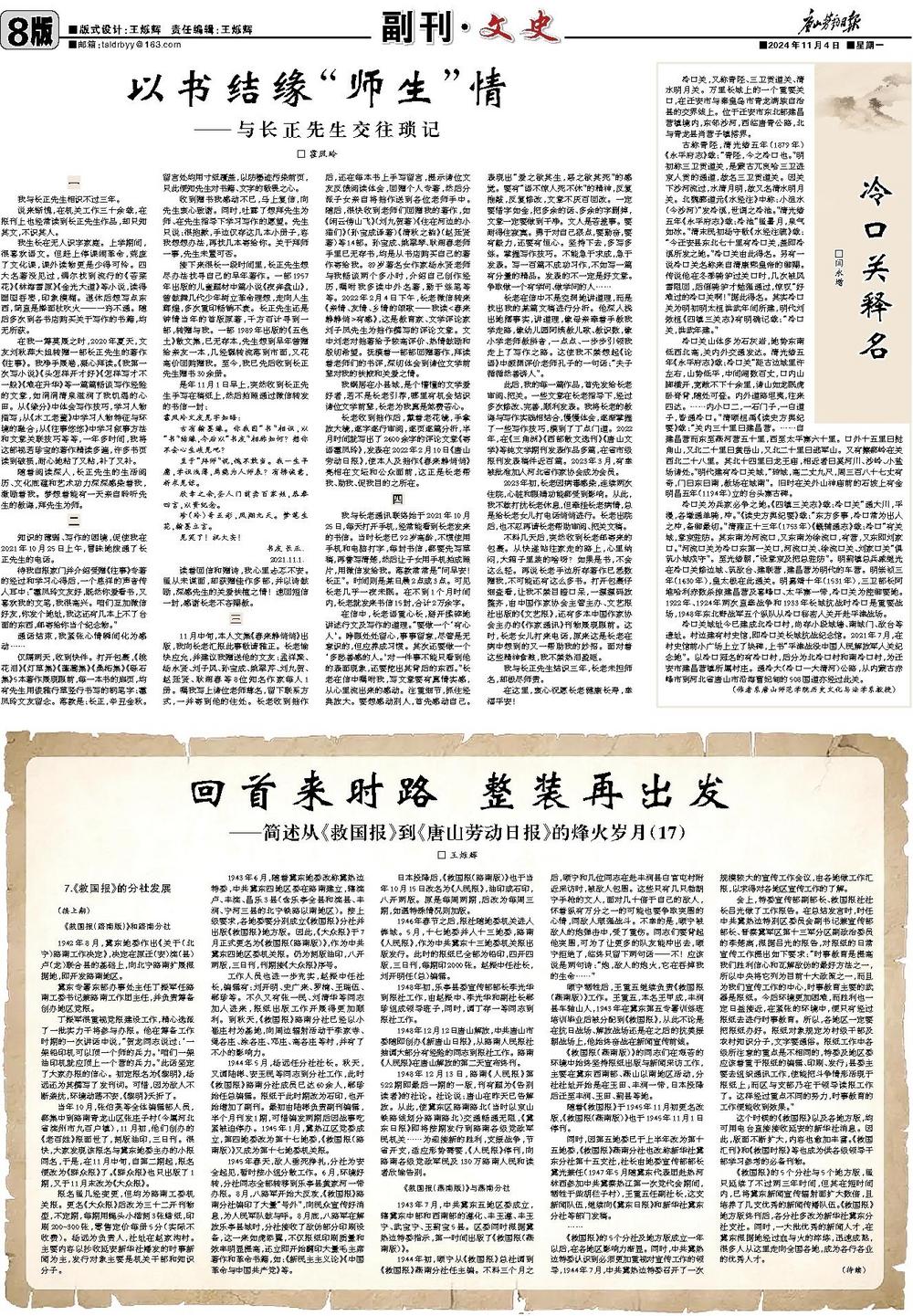□ 霍凤玲
一
我与长正先生相识不过三年。
说来惭愧,在机关工作三十余载,在报刊上也经常读到长正先生作品,却只知其文,不识其人。
我生长在无人识字家庭。上学期间,很喜欢语文。但赶上停课闹革命,荒废了文化课,课外读物更是少得可怜。四大名著没见过,偶尔找到流行的《苦菜花》《林海雪原》《金光大道》等小说,读得囫囵吞枣,印象模糊。退休后想写点东西,简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随后多次到各书店购买关于写作的书籍,均无所获。
在我一筹莫展之时,2020年夏天,文友刘秋萍大姐转赠一部长正先生的著作《往事》。我净手展卷,凝心拜读。《我第一次写小说》《头怎样开才好》《怎样写才不一般》《难在升华》等一篇篇畅谈写作经验的文章,如涓涓清泉滋润了我饥渴的心田。从《缘分》中体会写作技巧,学习人物描写;从《木工老董》中学习人物特征与环境的融合;从《往事悠悠》中学习叙事方法和文章关联技巧等等,一年多时间,我将这部视若珍宝的著作精读多遍,许多书页读到破损,耐心地粘了又粘,补了又补。
随着阅读深入,长正先生的生活阅历、文化底蕴和艺术功力深深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梦想着能有一天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拜先生为师。
二
知识的薄弱、写作的困境,促使我在2021年10月25日上午,冒昧地拨通了长正先生的电话。
待我自报家门并介绍受赠《往事》专著的经过和学习心得后,一个慈祥的声音传入耳中:“霍凤玲文友好,既然你爱看书,又喜欢我的文笔,我很高兴。咱们互加微信好友,你发个地址,我这还有几本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邮寄给你当个纪念物。”
通话结束,我紧张心情瞬间化为感动……
仅隔两天,收到快件。打开包裹,《桃花泪》《灯草集》《蓬蒿集》《桑柘集》《砾石集》5本著作展现眼前,每一本书的扉页,均有先生用俊雅行草竖行书写的钢笔字:霍凤玲文友留念。落款是:长正,辛丑金秋。留言处均用寸纸覆盖,以防墨迹污染前页,只此便知先生对书籍、文字的敬畏之心。
收到赠书我感动不已,马上复信,向先生衷心致谢。同时,吐露了想拜先生为师、在先生指导下学习写作的愿望。先生只说:很抱歉,手边仅存这几本小册子,容我想想办法,再找几本寄给你。关于拜师一事,先生未置可否。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长正先生想尽办法找寻自己的早年著作。一部1957年出版的儿童题材中篇小说《夜奔盘山》,曾鼓舞几代少年树立革命理想,走向人生辉煌,多次重印畅销不衰。长正先生还是钟情当年的首版原著,千方百计寻到一部,转赠与我。一部 1989年出版的《五色土》散文集,已无存本,先生想到早年曾赠给亲友一本,几经辗转流落到市面,又花高价回购赠我。至今,我已先后收到长正先生赠书30余册。
是年11月1日早上,突然收到长正先生手写在稿纸上,然后拍照通过微信转发的书信一封:
霍凤玲文友见字如晤:
古有翰墨缘。你我因“书”相识,以“书”结缘,今后以“书友”相称如何?想你不会心生歧见吧?
至于“拜师”说,愧不敢当。我一生平庸,学识浅薄,焉能为人师表?有拂诚意,祈求见谅。
欣幸之余,圣人门前卖百家姓,恭奉四言,以资纪念。
珍(玲)奇五彩,凤翔九天。梦笔生花,翰墨立言。
见笑了!祝大安!
书友 长正.
2021.11.1.
读着回信和赠诗,我心里忐忑不安。虽从未谋面,却获赠佳作多部,并以诗鼓励,深感先生的关爱扶植之情!速回短信一封,感谢长老不吝赐教。
三
11月中旬,本人文集《春来静悄悄》出版,我向长老汇报此事敬请雅正。长老愉快应允,并建议我赠送他的文友:孟祥聚、杨永贤、刘子风、孙宝成、姚翠芹、刘九贺、赵廷贤、耿湘春等8位知名作家每人1册。嘱我写上诸位老师尊名,留下联系方式,一并寄到他的住处。长老收到拙作后,还在每本书上手写留言,提示诸位文友反馈阅读体会,回赠个人专著,然后分派子女亲自将拙作送到各位老师手中。随后,很快收到老师们回赠我的著作,如《闲云傍山飞》(刘九贺著)《住在河边的小猫们》(孙宝成译著)《清秋之韵》(赵廷贤著)等14部。孙宝成、姚翠琴、耿湘春老师手里已无存书,均是从书店购买自己的著作寄给我。89岁著名女作家杨永贤老师与我畅谈两个多小时,介绍自己创作经历,嘱咐我多读中外名著,勤于练笔等等。2022年2月4日下午,长老微信转来《亲情、友情、乡情的颂歌——我读<春来静静悄>有感》,这是教育家、文学评论家刘子凤先生为拙作撰写的评论文章。文中刘老对拙著给予较高评价、热情鼓励和殷切希望。抚摸着一部部回赠著作,拜读着老师们的书评,深切体会到诸位文学前辈对我的扶掖和关爱之情。
我蜗居在小县城,是个懵懂的文学爱好者,若不是长老引荐,哪里有机会结识诸位文学前辈,长老为我真是煞费苦心。
长老收到拙作后,戴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逐字逐行审阅,逐页逐篇分析,半月时间就写出了2600余字的评论文章《寄语霍凤玲》,发表在2022年2月10日《唐山劳动日报》,使本人及拙作《春来静悄悄》亮相在文坛和公众面前,这正是长老帮我、助我、促我目的之所在。
四
我与长老通讯联络始于2021年10月25日,每天打开手机,经常能看到长老发来的书信。当时长老已92岁高龄,不惯使用手机和电脑打字,每封书信,都要先写草稿,再誊写清楚,然后让子女用手机拍成照片,用微信发给我。落款常常是“问早安!长正”。时间则是某日晨2点或3点。可见长老几乎一夜未眠。在不到1个月时间内,长老就发来书信15封,合计2万余字。
在信中,长老语重心长,掰开揉碎地讲述行文及写作的道理。“要做一个‘有心人’。睁眼处处留心,事事留意,尽管是无意识的,但应养成习惯。其次还要做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对一件事不能只看到他的表面现象,还要挖出其背后的东西。”长老在信中嘱咐我,写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从心里流出来的感动。注重细节,抓住经典放大。要想感动别人,首先感动自己。表现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感觉。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文章不厌百回改。一定要惜字如金,把多余的话、多余的字删掉,文章一定要做到干净。文人是苦差事。要耐得住寂寞。勇于对自己狠点,要勤奋,要有毅力,还要有恒心。坚持下去,多写多练。掌握写作技巧。不能急于求成,急于发表。写一百篇不成功习作,不如写一篇有分量的精品。发表的不一定是好文章。争取做一个有学问、做学问的人……
长老在信中不是空洞地讲道理,而是找出我的某篇文稿进行分析。他深入浅出地摆事实,讲道理,像母亲牵着手教我学走路,像幼儿园阿姨教儿歌、教识数,像小学老师教拼音,一点点、一步步引领我走上了写作之路。这使我不禁想起《论语》中颜渊评价老师孔子的一句话:“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此后,我的每一篇作品,首先发给长老审阅、把关。一些文章在长老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完善,顺利发表。我将长老的教诲与写作实践相结合,慢慢体会,逐渐掌握了一些写作技巧,摸到了丁点门道。2022年,在《三角洲》《西部散文选刊》《唐山文学》等纯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多篇,在省市级报刊发表稿件近百篇。2023年3月,有幸被批准加入河北省作家协会成为会员。
2023年初,长老因病毒感染,连续两次住院,心脏和眼睛功能都受到影响。从此,我不敢打扰长老休息,但牵挂长老病情,总是给长老女儿打电话悄悄进行。长老出院后,也不忍再请长老帮助审阅、把关文稿。
不料几天后,突然收到长老邮寄来的包裹。从快递站往家走的路上,心里纳闷,大箱子里装的啥呀?如果是书,不会这么轻。再说长老手边所存著作已悉数赠我,不可能还有这么多书。打开包裹仔细查看,让我不禁目瞪口呆,一摞摞码放整齐,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文艺报社出版的《文艺报》,还有多本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通讯》刊物展现眼前。这时,长老女儿打来电话,原来这是长老在病中想到的又一帮助我的妙招。面对着这些精神食粮,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与长正先生结识三年,长老未担师名,却极尽师责。
在这里,衷心祝愿长老健康长寿,幸福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