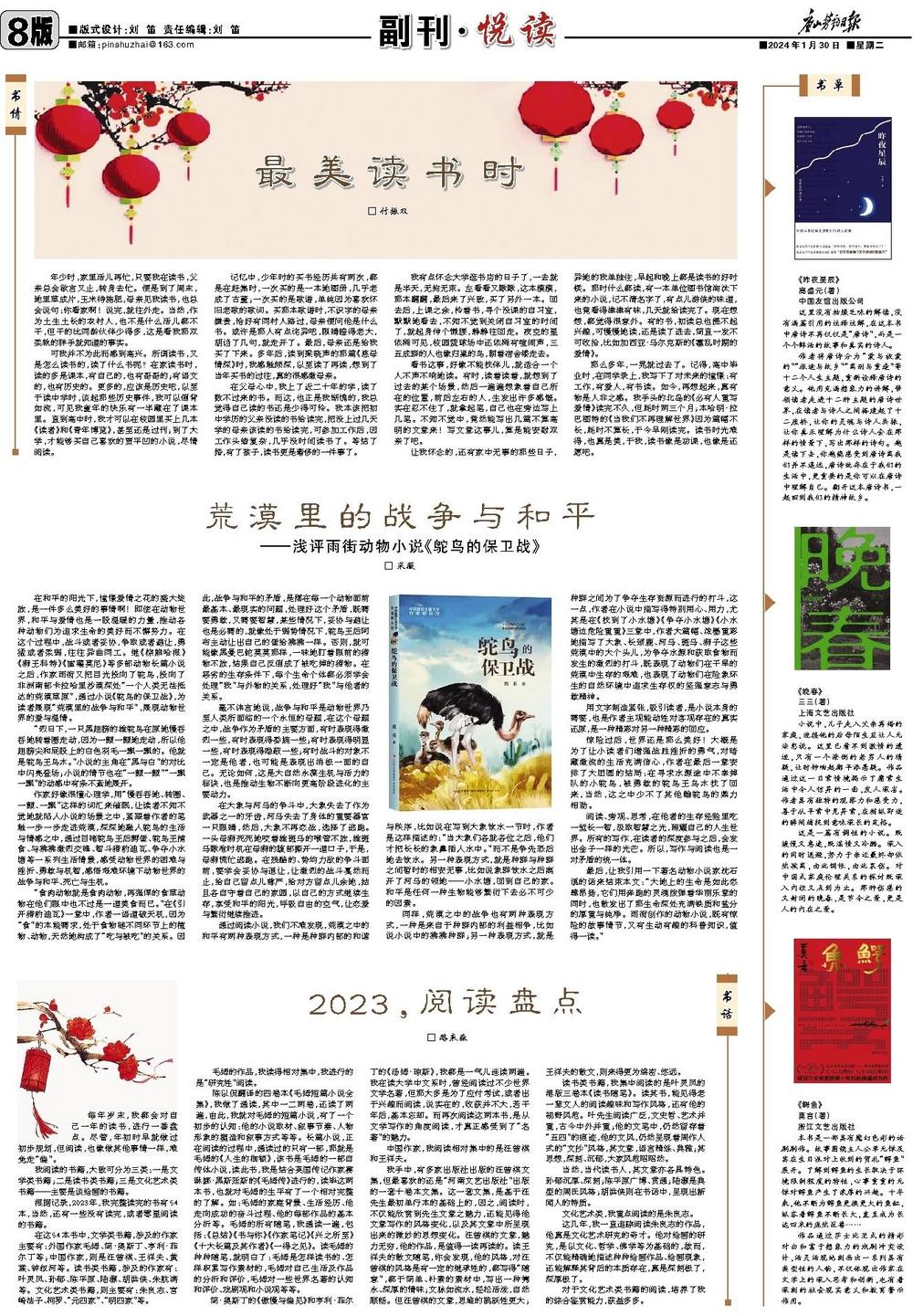年少时,家里活儿再忙,只要我在读书,父亲总会欲言又止,转身去忙。便是到了周末,地里草成片,玉米待施肥,母亲见我读书,也总会说句:你看家啊!说完,就往外走。当然,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也不是什么活儿都不干,但干的比同龄伙伴少得多,这是看我那双柔软的胖手就知道的事实。
可我并不为此而感到高兴。所谓读书,又是怎么读书的,读了什么书呢?在家读书时,读的多是课本,有自己的,也有哥哥的;有语文的,也有历史的。更多的,应该是历史吧,以至于读中学时,谈起那些历史事件,我可以倒背如流,可见我童年的快乐有一半藏在了课本里。直到高中时,我才可以在校园里买上几本《读者》和《青年博览》,甚至还是过刊;到了大学,才能够买自己喜欢的贾平凹的小说,尽情阅读。
记忆中,少年时的买书经历共有两次,都是在赶集时,一次买的是一本地图册,几乎老成了古董;一次买的是歌谱,单纯因为喜欢怀旧老歌的歌词。买那本歌谱时,不识字的母亲嫌贵,恰好有同村人路过,母亲便问他是什么书。或许是那人有点诧异吧,眼睛瞪得老大,胡诌了几句,就走开了。最后,母亲还是给我买了下来。多年后,读到梁晓声的那篇《慈母情深》时,我感触颇深,以至读了再读,想到了当年买书的过往,真的很感激母亲。
在父母心中,我上了近二十年的学,读了数不过来的书。而这,也正是我惭愧的,我总觉得自己读的书还是少得可怜。我本该把初中学历的父亲没读的书给读完,把没上过几天学的母亲该读的书给读完,可参加工作后,因工作头绪复杂,几乎没时间读书了。等结了婚,有了孩子,读书更是奢侈的一件事了。
我有点怀念大学逛书店的日子了,一去就是半天,无拘无束。左看看又瞅瞅,这本摸摸,那本翻翻,最后来了兴致,买了另外一本。回去后,上课之余,拎着书,寻个没课的自习室,默默地看去,不知不觉到关闭自习室的时间了,就起身伸个懒腰,静静往回走。夜空的星依稀可见,校园篮球场中还依稀有喧闹声,三五成群的人也像归巢的鸟,朝着宿舍楼走去。
看书这事,好像不能找伴儿,就适合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读。有时,读着读着,就想到了过去的某个场景,然后一遍遍想象着自己所在的位置,前后左右的人,生发出许多感慨。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起笔,自己也在旁边写上几笔。不知不觉中,竟然能写出几篇不算高明的文章来!写文章这事儿,算是能安慰双亲了吧。
让我怀念的,还有家中无事的那些日子,异地的我单独住,早起和晚上都是读书的好时候。那时什么都读,有一本单位图书馆淘汰下来的小说,记不清名字了,有点儿游侠的味道,也竟看得津津有味,几天就给读完了。现在想想,都觉得很意外。有的书,初读总也提不起兴趣,可慢慢地读,还是读了进去,简直一发不可收拾,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那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记得,高中毕业时,在同学录上,我写下了对未来的憧憬:有工作,有爱人,有书读。如今,再想起来,真有物是人非之感。我手头的北岛的《必有人重写爱情》读完不久,但耗时两三个月;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因为篇幅不长,耗时不算长,于今早刚读完。读书时光难得,也真是美,于我,读书像是功课,也像是还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