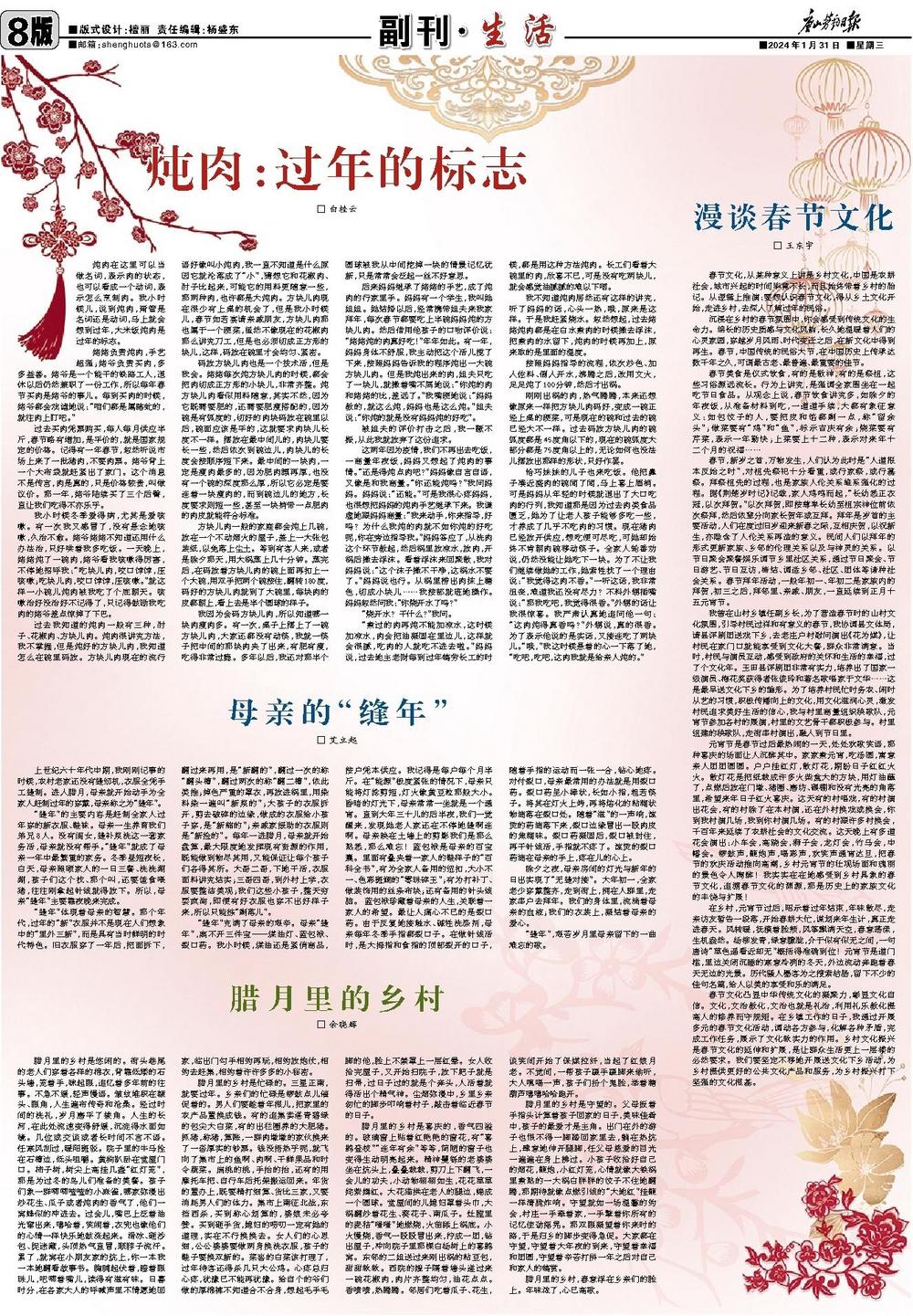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农村老家还没有缝纫机,衣服全凭手工缝制。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动手为全家人赶制过年的穿戴,母亲称之为“缝年”。
“缝年”的主要内容是赶制全家人过年穿的新衣服、鞋袜。母亲一生养育我们弟兄8人。没有闺女,缝补浆洗这一套家务活,母亲就没有帮手。“缝年”就成了母亲一年中最繁重的家务。冬季昼短夜长,白天,母亲照顾家人的一日三餐、洗洗涮涮,孩子们这个找、那个叫,还要馇食喂猪,往往刚拿起针线就得放下。所以,母亲“缝年”主要靠夜晚来完成。
“缝年”体现着母亲的智慧。那个年代,过年的“新”衣服并不是现在人们想象中的“里外三新”,而是具有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旧衣服穿了一年后,把面拆下,翻过来再用,是“新翻的”,翻过一次的称“翻头槽”,翻过两次的称“翻二槽”,依此类推;掉色严重的罩衣,再放进锅里,用染料染一遍叫“新浆的”;大孩子的衣服拆开,剪去破碎的边缘,做成的衣服给小孩子穿,是“新缩的”;亲戚家援助的衣服则是“新捡的”。每年一进腊月,母亲就开始盘算,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既能做到物尽其用,又能保证让每个孩子们各得其所。大哥二哥,下地干活,衣服面料讲究结实;三哥四哥,到外村上学,衣服要整洁美观;我们这些小孩子,整天穷耍疯淘,即便有好衣服也穿不出好样子来,所以只能拣“剩落儿”。
“缝年”充满了母亲的艰辛。母亲“缝年”,离不开三件宝——煤油灯、蓝包袱、裂口药。我小时候,煤油还是紧俏商品,按户凭本供应。我记得是每户每个月半斤。在“能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母亲只能将灯捻剪短,灯火像黄豆粒那般大小。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常常一坐就是一个通宵。直到大年三十儿的后半夜,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她老人家还在不停地缝啊连啊。母亲映在土墙上的剪影我们是那么熟悉,那么难忘!蓝包袱是母亲的百宝囊。里面有叠夹着一家人的鞋样子的“百科全书”,有为全家人备用的纽扣,大小不一、色彩斑斓的“零珠碎玉”;有为打补丁、做装饰用的丝条布块;还有备用的针头线脑。 蓝包袱珍藏着母亲的人生,关联着一家人的希望。最让人痛心不已的是裂口药。由于反复地接触水、碱性洗涤剂,母亲每年冬季手指都裂口子。在做针线活时,是大拇指和食指的顶部裂开的口子,随着手指的运动而一张一合,钻心地疼。对付裂口,母亲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用裂口药。裂口药呈小棒状,长如小指,粗若筷子。将其在灯火上烤,再将熔化的粘糊状物滴落在裂口处。随着“滋”的一声响,滚烫的药滴落下来,裂口边缘冒出一股肉皮的焦糊味。裂口药凝固后,裂口被封住,再干针线活,手指就不疼了。滚烫的裂口药滴在母亲的手上,疼在儿的心上。
除夕之夜,母亲房间的灯光与新年的日出实现了“无缝对接”。大年初一,全家老少穿戴整齐,走到街上,拥在人群里,走家串户去拜年。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着母亲的血液;我们的衣装上,凝结着母亲的爱心。
“缝年”,艰苦岁月里母亲留下的一曲难忘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