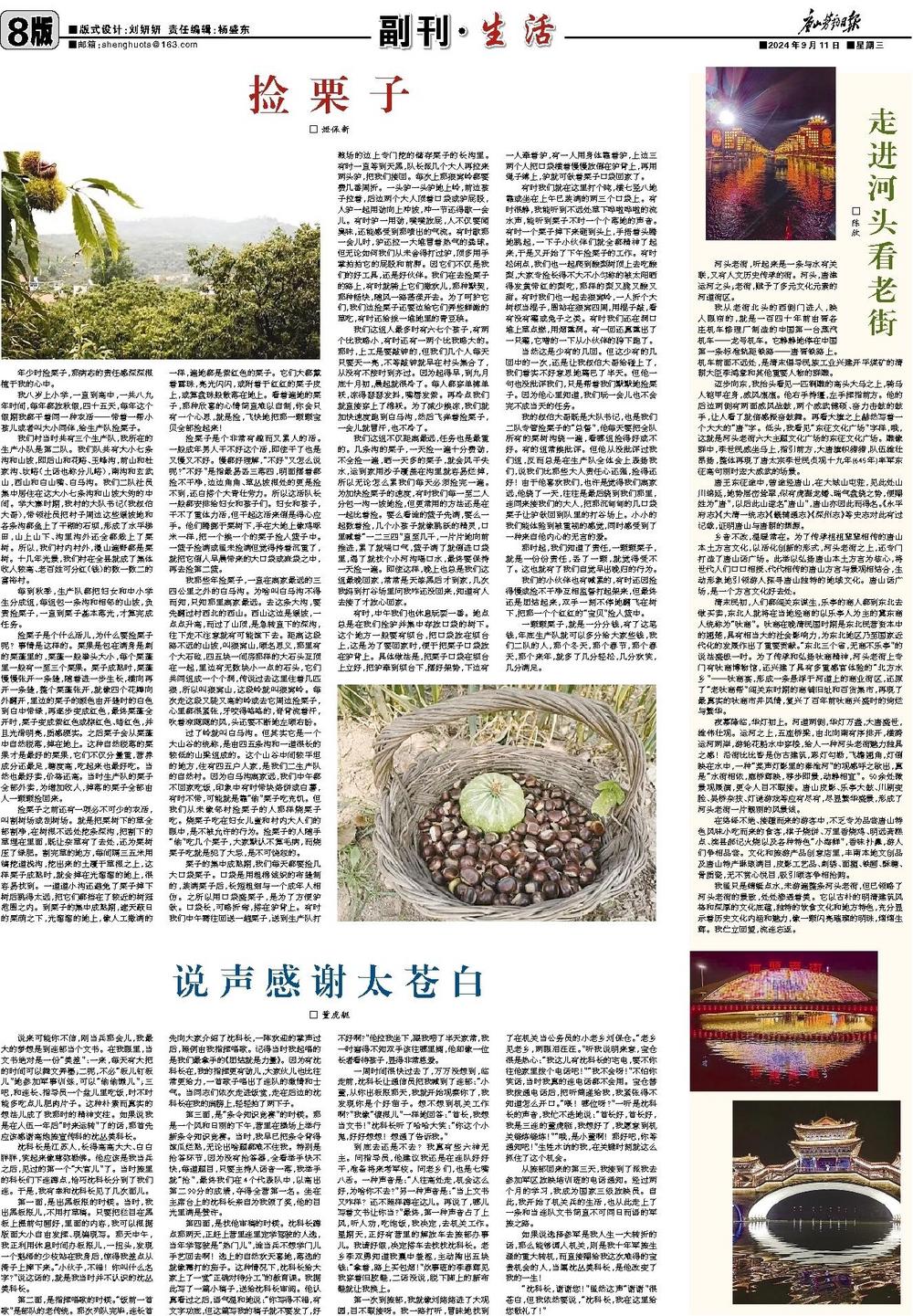年少时捡栗子,那病态的责任感深深根植于我的心中。
我八岁上小学,一直到高中,一共八九年时间,每年都放秋假,四十五天,每年这个假期我都干着同一种农活——带着一帮小孩儿或者叫大小同伴,给生产队捡栗子。
我们村当时共有三个生产队,我所在的生产小队是第二队。我们队共有大小七条沟和山坡,即后山和花峪、玉峰沟,前山和杜家沟、坟峪(土话也称分儿峪),南沟和玄武山,西山和白山嘴、白马沟。我们二队社员集中居住在这大小七条沟和山坡大约的中间。学大寨时期,我村的大队书记(我叔伯大哥),带领社员把村子周边这些缓坡地和各条沟都垒上了干砌的石坝,形成了水平梯田,山上山下、沟里沟外还全都栽上了栗树。所以,我们村内村外,漫山遍野都是栗树。十几年光景,我们村在全县就成了集体收入较高、老百姓可分红(钱)的数一数二的富裕村。
每到秋季,生产队都把妇女和中小学生分成组,每组包一条沟和相邻的山坡,负责捡栗子,一直到栗子基本落光,才算完成任务。
捡栗子是个什么活儿,为什么要捡栗子呢?事情是这样的。栗果是包在满身是刺的栗蓬里的,栗蓬一般拳头大小,每个栗蓬里一般有一至三个栗果。栗子成熟时,栗蓬慢慢张开一条缝,随着进一步生长,横向再开一条缝,整个栗蓬张开,就像四个花瓣向外翻开,里边的栗子的颜色由开缝时的白色到白中带绿,再逐步变成红色,最终栗蓬全开时,栗子变成紫红色或棕红色、暗红色,并且光滑明亮,质感硬实。之后栗子会从栗蓬中自然脱落,掉在地上。这种自然脱落的栗果才是最好的栗果,它们不仅分量重,营养成分还最足,糖度高,吃起来也最好吃。当然也最好卖,价格还高。当时生产队的栗子全部外卖,为增加收入,掉落的栗子全部由人一颗颗捡回来。
捡栗子之前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农活,叫割树场或刮树场。就是把栗树下的草全部割净,在树根不远处挖条深沟,把割下的草埋在里面,既让杂草有了去处,还为栗树压了绿肥。割完草的地方,每间隔三五米用镐挖道浅沟,挖出来的土覆于草根之上,这样栗子成熟时,就会掉在光溜溜的地上,很容易找到。一道道小沟还避免了栗子掉下树后跳得太远,把它们都挡在了较近的树冠范围之内。到栗子的集中成熟期,遮天蔽日的栗荫之下,光溜溜的地上,像人工撒满的一样,遍地都是紫红色的栗子。它们大都戴着露珠,亮光闪闪,或附着于红红的栗子皮上,或算盘珠般散落在地上。看着遍地的栗子,那种欣喜的心情简直难以自制,你会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捡,飞快地把那一颗颗宝贝全部捡起来!
捡栗子是个非常有趣而又累人的活。一般成年男人干不好这个活,即使干了也是又慢又不好。慢都好理解,“不好”又怎么说呢?“不好”是指最易丢三落四,明面摆着都捡不干净,边边角角、草丛坡根处的更是捡不到,还白搭个大青壮劳力。所以这活队长一般都安排给妇女和孩子们。妇女和孩子,干不了重体力活,但干起这活来倒是得心应手。他们腾挪于栗树下,手在大地上像鸡啄米一样,把一个挨一个的栗子捡入篮子中。一篮子捡满或虽未捡满但觉得挎着沉重了,就把它倒入早晨带来的大口袋或麻袋之中,再去捡第二篮。
我那些年捡栗子,一直在离家最远的三四公里之外的白马沟。为啥叫白马沟不得而知,只知那里离家最远。去这条大沟,要先翻过村西北的西山。西山这边是缓坡,一点点升高,而过了山顶,是急转直下的深沟,往下走不注意就有可能滚下去。距离这段路不远的山坡,叫狼窝山,顾名思义,那里有个大石砬,四五块一间房那样的大石头互顶在一起,里边有无数块小一点的石头,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个洞,传说过去这里住着几匹狼,所以叫狼窝山,这段岭就叫狼窝岭。每次走这段又陡又高的岭或去它周边捡栗子,心里都很紧张,牙咬得咯咯的,脊背流着汗,吹着凉飕飕的风,头还要不断地左顾右盼。
过了岭就叫白马沟。但其实它是一个大山谷的统称,是由四五条沟和一道很长的较低的山梁组成的。这个山谷中间较平坦的地方,住有四五户人家,是我们二生产队的自然村。因为白马沟离家远,我们中午都不回家吃饭,印象中有时带块烙饼或白薯,有时不带,可能就是靠“偷”栗子吃充饥。但我们从未像邻村捡栗子的人那样烧栗子吃。烧栗子吃在妇女儿童和村内大人们的眼中,是不被允许的行为。捡栗子的人随手“偷”吃几个栗子,大家默认不算毛病,而烧栗子吃就是犯了大忌,是不可饶恕的。
栗子的集中成熟期,我们每天都要捡几大口袋栗子。口袋是用粗棉线织的布缝制的,装满栗子后,长短粗细与一个成年人相仿。之所以用口袋盛栗子,是为了方便驴驮。口袋长,可略折弯,搭在驴背上。有时我们中午需往回送一趟栗子,送到生产队打粮场的边上专门挖的储存栗子的长沟里。有时一直等到天黑,队长派几个大人再拉来两头驴,把我们接回。每次上那狼窝岭都要费几番周折。一头驴一头驴地上岭,前边孩子拉着,后边两个大人顶着口袋或驴屁股,人驴一起用劲向上冲坡,冲一节还得歇一会儿。有时驴一用劲,噗噗放屁,人不仅要闻臭味,还能感受到那喷出的气流。有时歇那一会儿时,驴还拉一大堆冒着热气的粪球。但无论如何我们从未舍得打过驴,顶多用手掌拍拍它的屁股和前胛。因它们不仅是我们的好工具,还是好伙伴。我们在去捡栗子的路上,有时就骑上它们撒欢儿,那种默契,那种畅快,随风一路荡漾开去。为了呵护它们,我们边捡栗子还要边给它们弄些鲜嫩的草吃,有时还给拔一堆地里的青豆秧。
我们这组人最多时有六七个孩子,有两个比我略小,有时还有一两个比我略大的。那时,上工是要敲钟的,但我们几个人每天只要天一亮,不等敲钟就早在村头集合了,从没有不按时到齐过。因为起得早,到九月底十月初,晨起就很冷了。每人都穿单裤单袄,冻得瑟瑟发抖,嘴唇发紫。再冷点我们就直接穿上了棉袄。为了减少挨冻,我们就加快速度跑到白马沟,然后飞奔着捡栗子,一会儿就冒汗,也不冷了。
我们这组不仅距离最远,任务也是最重的。几条沟的栗子,一天捡一遍十分费劲,不全捡一遍,晒一天多的栗子,就会风干失水,运到家用沙子覆盖在沟里就容易烂掉,所以无论怎么累我们每天必须捡完一遍。为加快捡栗子的速度,有时我们每一至二人分包一沟一坡地捡,但更常用的方法还是在一起比着捡。要么看谁的篮子先满,要么一起数着捡,几个小孩子就像跳跃的精灵,口里喊着“一二三四”直至几千,一片片地向前推进,累了就喘口气,篮子满了就倒进口袋里,渴了就找个小河沟喝口水,最终要保持一天捡一遍。即使这样,晚上也总是我们这组最晚回家,常常是天漆黑后才到家,几次我妈到打谷场里问我咋还没回来,知道有人去接了才放心回家。
有时,中午我们也休息玩耍一番。地点总是在我们拴驴并集中存放口袋的树下。这个地方一般要有坝台,把口袋放在坝台上,这是为了要回家时,便于把栗子口袋放在驴背上。具体做法是,把栗子口袋在坝台上立好,把驴牵到坝台下,摆好架势,下边有一人牵着驴,有一人用身体靠着驴,上边三两个人把口袋横着慢慢放倒在驴背上,再用绳子缚上,驴就可驮着栗子口袋回家了。
有时我们就在这里打个盹,横七竖八地靠或坐在上午已装满的两三个口袋上。有时很静,我能听到不远处草下哗啦哗啦的流水声,能听到栗子不时一个个落地的声音。有时一个栗子掉下来砸到头上,手捂着头腾地跳起,一下子小伙伴们就全都精神了起来,于是又开始了下午捡栗子的工作。有时松闲点,我们也一起爬到酸梨树顶上去吃酸梨,大家专捡长得不大不小匀称的被太阳晒得发黄带红的梨吃,那样的梨又脆又酸又甜。有时我们也一起去狼窝岭,一人折个大树杈当棍子,围站在狼窝四周,用棍子敲,看有没有獾或兔子之类。有时我们还在洞口堆上草点燃,用烟熏洞。有一回还真熏出了一只獾,它噌的一下从小伙伴的胯下跑了。
当然这是少有的几回。但这少有的几回中的一次,还是让我叔伯大哥给碰上了,我们着实不好意思地蔫巴了半天。但他一句也没批评我们,只是帮着我们默默地捡栗子。因为他心里知道,我们玩一会儿也不会完不成当天的任务。
我的叔伯大哥既是大队书记,也是我们二队专管捡栗子的“总督”,他每天要把全队所有的栗树沟绕一遍,看哪组捡得好或不好。有的组常挨批评。但他从没批评过我们组,反而总是在生产队全体会上表扬我们,说我们比那些大人责任心还强,捡得还好!由于他喜欢我们,也许是觉得我们离家远,他绕了一天,往往是最后绕到我们那里,连同来接我们的大人,把那沉甸甸的几口袋栗子让驴驮回到队里的打谷场上。小小的我们能体验到被重视的感觉,同时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他内心的无言的爱。
那时起,我们知道了责任,一颗颗栗子,就是一份份责任,丢了一颗,就觉得受不了。这也就有了我们自觉早出晚归的行为。
我们的小伙伴也有喊累的,有时还因捡得慢或捡不干净互相监督打起架来,但最终还是团结起来,双手一刻不停地翻飞在树下,把那一个个红红的“宝贝”捡入篮中。
一颗颗栗子,就是一分分钱,有了这笔钱,年底生产队就可以多分给大家些钱,我们二队的人,那个冬天,那个春节,那个春天,那个来年,就多了几分轻松,几分欢笑,几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