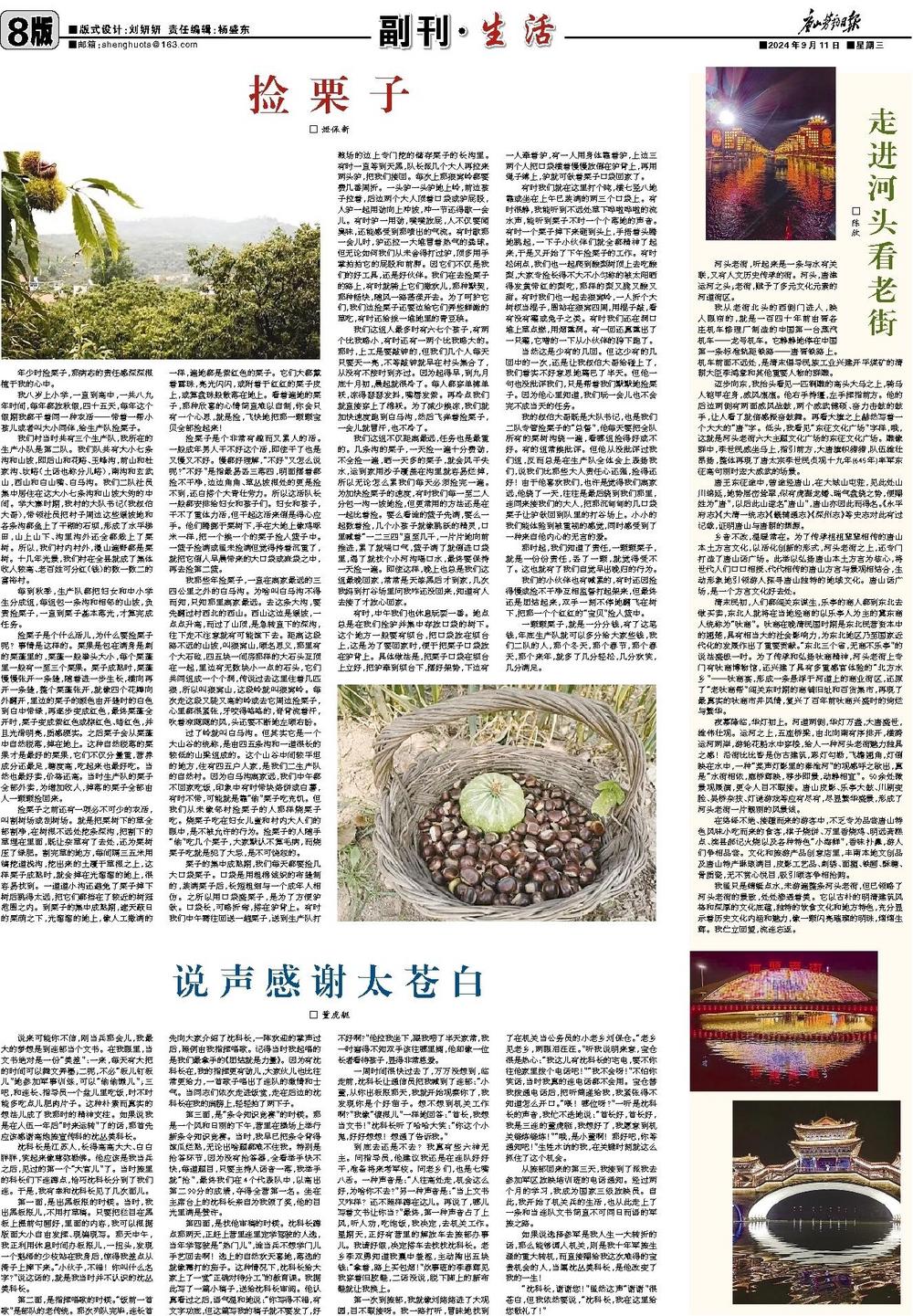说来可能你不信,刚当兵那会儿,我最大的梦想是到连部当个文书。在我眼里,当文书绝对是一份“美差”:一来,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舞文弄墨;二呢,不必“板儿钉板儿”地参加军事训练,可以“偷偷懒儿”;三吧,和连长、指导员一个盆儿里吃饭,时不时能多吃点儿肥肉片子。这种朴素而真实的想法儿成了我那时的精神支柱。如果说我是在入伍一年后“时来运转”了的话,那首先应该感谢高炮旅宣传科的沈丛美科长。
沈科长是江苏人,长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笑起来像尊弥勒佛。他应该是我当兵之后,见过的第一个“大官儿”了。当时旅里的科长们下连蹲点,恰巧沈科长分到了我们连。于是,我有幸和沈科长见了几次面儿。
第一面,是出黑板报的时候。当时,我出黑板报儿,不用打草稿。只要把栏目在黑板上提前勾画好,里面的内容,我可以根据版面大小自由发挥、现编现写。那天中午,我正利用休息时间办板报儿,一扭头,发现一个魁梧的少校站在我身后,惊得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小伙子,不错!你叫什么名字?”说这话的,就是我当时并不认识的沈丛美科长。
第二面,是指挥唱歌的时候。“饭前一首歌”是部队的老传统。那次列队完毕,连长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沈科长,一阵欢迎的掌声过后,照例由我指挥唱歌。记得当时我起唱的是我们最拿手的《团结就是力量》。因为有沈科长在,我的指挥更有劲儿,大家伙儿也比往常更给力,一首歌子唱出了连队的激情和士气。当同志们依次走进饭堂,走在后边的沈科长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子。
第三面,是“条令知识竞赛”的时候。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营里在操场上举行新条令知识竞赛。当时,我早已把条令背得滚瓜烂熟,无论出啥题都难不住我。特别是抢答环节,因为没有抢答器,全看举手快不快,每道题目,只要主持人话音一落,我举手就“抢”,最终我们在4个代表队中,以高出第二90分的成绩,夺得全营第一名。坐在主席台上的沈科长亲自为我颁了奖,他的目光里满是赞许。
第四面,是找他审稿的时候。沈科长蹲点那两天,正赶上营里连里定学驾驶的人选,当年学驾驶是“热门儿”,谁当兵不想学门儿手艺回去啊!选上的自然欢天喜地,落选的就像霜打的茄子。这种情况下,沈科长给大家上了一堂“正确对待分工”的教育课。我据此写了一篇小稿子,送给沈科长审阅。他认真看过之后,语气温和地说:“你写得不错,有文字功底,但这篇写我的稿子就不要发了,好不好啊?”他拉我坐下,跟我唠了半天家常,我一时窘得不知双手该往哪里搁,他却像一位长者看待孩子,显得非常慈爱。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万万没想到,临走前,沈科长让通信员把我喊到了连部:“小董,从你出板报那天,我就开始观察你了,我发现你是个好苗子。想不想到机关工作啊?”我像“傻根儿”一样地回答:“首长,我想当文书!”沈科长听了哈哈大笑:“你这个小鬼,好好想想!想通了告诉我。”
到底去还是不去?我真有些六神无主。问指导员,他建议我还是在连队好好干,准备将来考军校。问老乡们,也是七嘴八舌。一种声音是:“人往高处走,机会这么好,为啥你不去?”另一种声音是:“当上文书又咋样?还不照样蹲在这儿。再说了,哪儿写着文书让你当?”最终,第一种声音占了上风,听人劝,吃饱饭,我决定,去机关工作。星期天,正好有营里的解放车去旅部办事儿。我请好假,决定搭车去找找沈科长。老乡李双勇知道我囊中羞涩,主动掏出五块钱:“拿着,路上买包烟!”炊事班的李春辉见我穿着旧胶鞋,二话没说,脱下脚上的新布鞋就让我换上。
第一次到旅部,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目不暇接呀。我一路打听,冒昧地找到了在机关当公务员的小老乡刘保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听我说明来意,宝仓很是热心:“我这儿有沈科长的宅电,要不你往他家里拨个电话吧!”“我不会呀!”不怕你笑话,当时我真的连电话都不会用。宝仓替我拨通电话后,把听筒递给我,我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开口。“喂!哪位呀?”一听是沈科长的声音,我忙不迭地说:“首长好,首长好,我是三连的董虎艇,我想好了,我愿意到机关锻炼锻炼!”“哦,是小董啊!那好吧,你等通知吧!”生性木讷的我,在关键时刻就这么抓住了这个机会。
从旅部回来的第三天,我接到了派我去参加军区放映培训班的电话通知。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成为国家三级放映员。自此,我开始了机关兵的生活,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和当连队文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的军旅之路。
如果说选择参军是我人生一大转折的话,那么能够调入机关,则是我十年军旅生涯的重大转机,而直接赐给我这次难得的宝贵机会的人,当属沈丛美科长,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沈科长,谢谢您!”虽然这声“谢谢”很苍白,但我依然要说,“沈科长,我在这里给您敬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