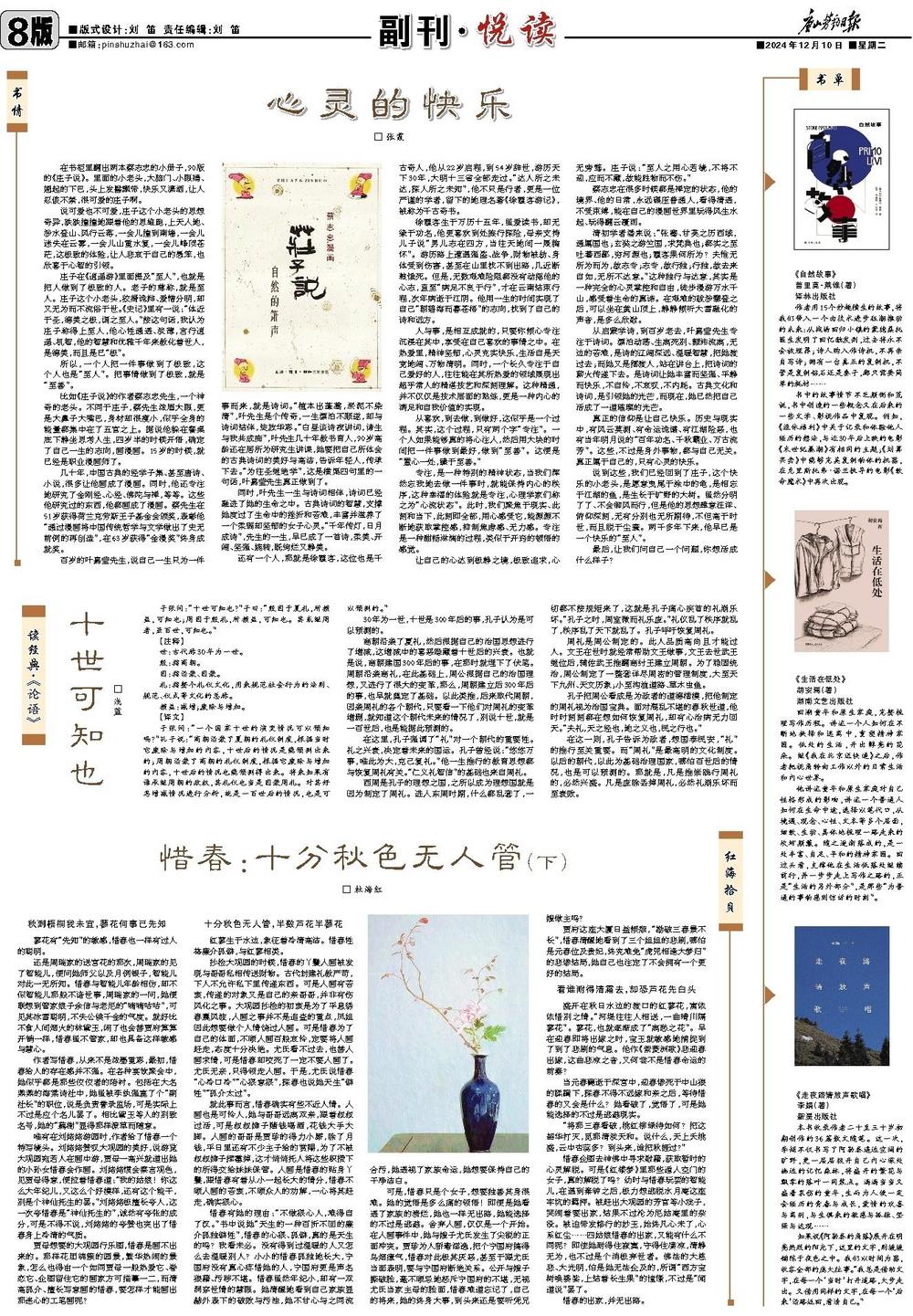秋到梧桐我未宜,蓼花何事已先知
蓼花有“先知”的敏感,惜春也一样有过人的聪明。
还是周瑞家的送宫花的那次,周瑞家的见了智能儿,便问她师父以及月例银子,智能儿对此一无所知。惜春与智能儿年龄相仿,却不似智能儿那般不谙世事,周瑞家的一问,她便联想到管家娘子余信与老尼的“嘀嘀咕咕”,可见其冰雪聪明,不失公侯千金的气度。就好比不食人间烟火的林黛玉,闲了也会替贾府算算开销一样,惜春虽不管家,却也具备这样敏感与慧心。
作者写惜春,从来不是浓墨重彩,最初,惜春给人的存在感并不强。在各种宴饮聚会中,她似乎都是那些佼佼者的陪衬。包括在大名鼎鼎的海棠诗社中,她虽被李纨强塞了个“副社长”的职位,说是负责誊录监场,可是实际上不过是应个名儿罢了。相比黛玉等人的别致名号,她的“藕榭”显得那样潦草而随意。
唯有在刘姥姥游园时,作者给了惜春一个特写镜头。刘姥姥赞叹大观园的美好,说游览大观园宛若人在画中游,贾母一高兴就道出她的小孙女惜春会作画。刘姥姥惯会察言观色,见贾母得意,便拉着惜春道:“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还有这个能干,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刘姥姥极擅长夸人,这一次夸惜春是“神仙托生的”,诚然有夸张的成分,可是不得不说,刘姥姥的夸赞也突出了惜春身上冷清的气质。
贾母想要的大观园行乐图,惜春是画不出来的。那样花团锦簇的园景,繁华热闹的景象,怎么也得由一个如同贾母一般热爱它、眷恋它、企图留住它的画家方可描摹一二,而清高孤介、擅长写意画的惜春,要怎样才能画出那违心的工笔画呢?
十分秋色无人管,半数芦花半蓼花
红蓼生于水边,象征着冷清高洁。惜春性格廉介孤僻,与红蓼相类。
抄检大观园的时候,惜春的丫鬟入画被发现与哥哥私相传送财物。古代封建礼教严苛,下人不允许私下里传递东西。可是入画有苦衷,传递的对象又是自己的亲哥哥,并非有伤风化之事。大观园抄检的初衷是为了平息绣春囊风波,入画之事并不是追查的重点,凤姐因此想要做个人情饶过入画。可是惜春为了自己的体面,不顾入画百般哀怜,定要将入画赶走,态度十分决绝。尤氏看不过去,也替入画求情,可是惜春却咬死了一定不要入画了。尤氏无奈,只得领走入画。于是,尤氏说惜春“心冷口冷”“心狠意狠”,探春也说她天生“僻性”“孤介太过”。
就此事而言,惜春确实有些不近人情。入画也是可怜人,她与哥哥远离双亲,跟着叔叔过活,可是叔叔婶子赌钱喝酒,花钱大手大脚。入画的哥哥是贾珍的得力小厮,除了月钱,平日里还有不少主子给的赏赐,为了不被叔叔婶子挥霍掉,这才悄悄托人将这些积攒下的所得交给妹妹保管。入画是惜春的贴身丫鬟,跟惜春有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惜春不顾入画的苦衷,不顾众人的劝解,一心将其赶走,确实狠心。
惜春有她的理由:“不做狠心人,难得自了汉。”书中说她“天生的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惜春的心狠、孤僻,真的是天生的吗?我看未必。没有得到过温暖的人又怎么去温暖别人?小小的惜春孤独地长大,宁国府没有真心疼惜她的人,宁国府更是声名狼藉、污秽不堪。惜春虽然年纪小,却有一双洞穿世情的慧眼。她清醒地看到自己家族显赫外表下的破败与污浊,她不甘心与之同流合污,她透视了家族命运,她想要保持自己的干净洁白。
可是,惜春只是个女子,想要独善其身很难。她的觉悟是多么痛的领悟!即便是她看透了家族的溃烂,她也一样无出路,她能选择的不过是逃避。舍弃入画,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入画事件中,她与嫂子尤氏发生了尖锐的正面冲突。贾珍为人骄奢淫逸,把个宁国府搞得乌烟瘴气,惜春对此极其厌恶,甚至于跟尤氏当面表明,要与宁国府断绝关系。公开与嫂子撕破脸,毫不顾忌地怒斥宁国府的不堪,无视尤氏当家主母的脸面,惜春难道忘记了,自己的将来,她的终身大事,到头来还是要听凭兄嫂做主吗?
贾府这座大厦日益倾颓,“勘破三春景不长”,惜春清醒地看到了三个姐姐的悲剧,哪怕是元春位及贵妃,终究难免“虎兕相逢大梦归”的悲惨结局,她自己也注定了不会拥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看谁耐得清霜去,却恐芦花先白头
盛开在秋日水边的渡口的红蓼花,寓依依惜别之情。“河堤往往人相送,一曲晴川隔蓼花”。蓼花,也就逐渐成了“离愁之花”。早在迎春即将出嫁之时,宝玉就敏感地捕捉到了到了悲剧的气息。他作《紫菱洲歌》悲迎春出嫁,这曲悲凉之音,又何尝不是惜春命运的前奏?
当元春薨逝于深宫中,迎春惨死于中山狼的蹂躏下,探春不得不远嫁和亲之后,等待惜春的又会是什么?她看破了,觉悟了,可是她能选择的不过是逃避现实。
“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
惜春企图去神佛中寻求慰藉,获取暂时的心灵解脱。可是《红楼梦》里那些遁入空门的女子,真的解脱了吗?幼时与惜春玩耍的智能儿,在遇到秦钟之后,极力想逃脱水月庵这座牢坑的羁押。被赶出大观园的芳官等小戏子,哭闹着要出家,结果不过沦为尼姑庵里的杂役。被迫带发修行的妙玉,始终凡心未了,心系红尘……四姑娘惜春的出家,又能有什么不同呢?即使她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凄凉,清静无为,也不过是个消极弃世者。佛法的大慈悲、大光明,怕是她无法企及的,所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的憧憬,不过是“闻道说”罢了。
惜春的出家,并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