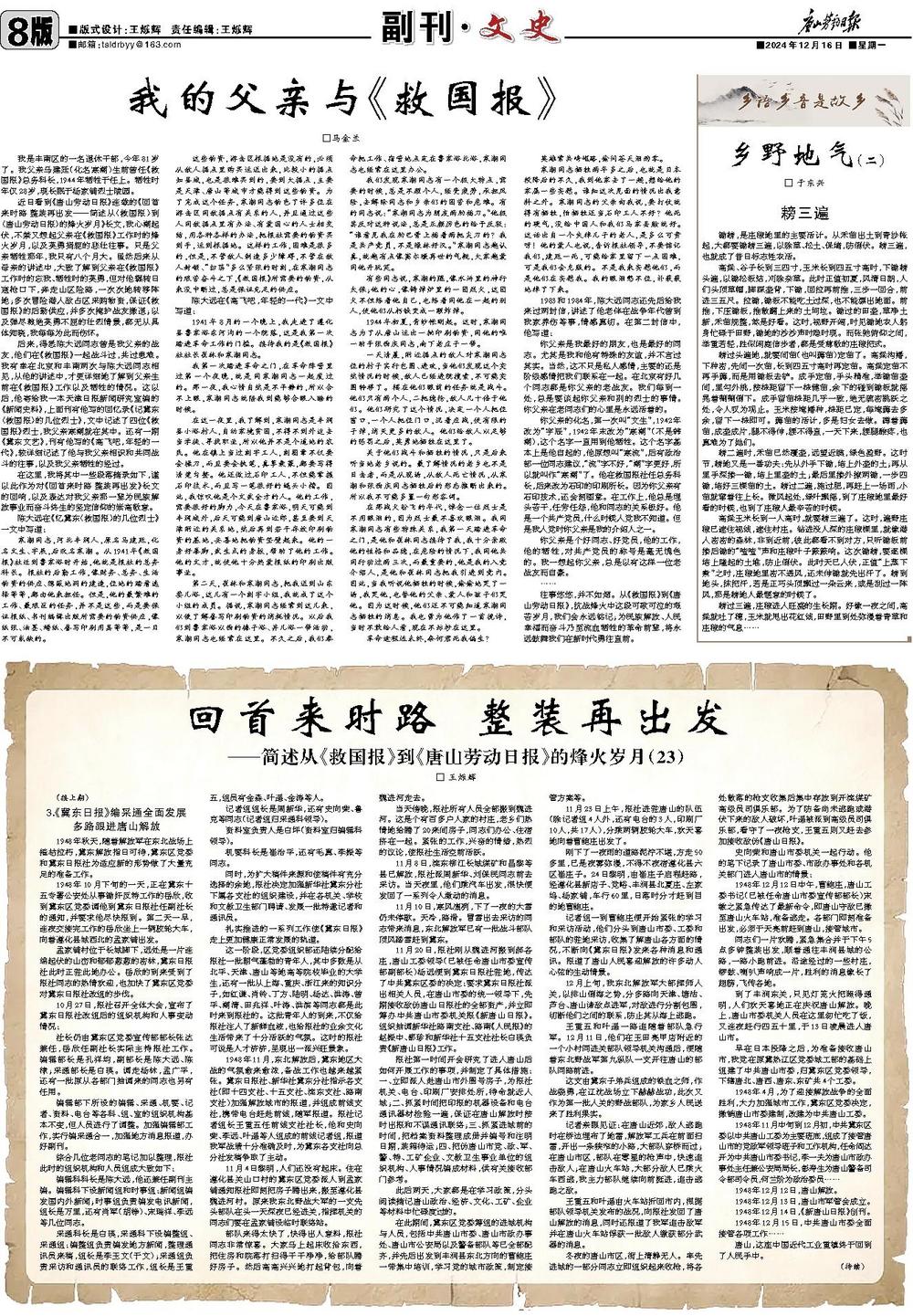我是丰南区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81岁了。我父亲马建廷(化名寒潮)生前曾任《救国报》总务科长,1944年牺牲于任上。牺牲时年仅28岁,现长眠于杨家铺烈士陵园。
近日看到《唐山劳动日报》连载的《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长文,我心潮起伏,不禁又想起父亲在《救国报》工作时的烽火岁月,以及英勇捐躯的悲壮往事。只是父亲牺牲那年,我只有八个月大。虽然后来从母亲的讲述中,大致了解到父亲在《救国报》工作时的忘我、牺牲时的英勇,但对他辗转日寇枪口下,奔走山区险路,一次次地转移阵地;多次冒险潜入敌占区采购物资,保证《救国报》的后勤供应,并多次掩护战友撤退;以及弹尽粮绝英勇不屈的壮烈情景,都无从具体知晓,我每每为此而伤怀。
后来,得悉陈大远同志曾是我父亲的战友,他们在《救国报》一起战斗过,共过患难。我有幸在北京和丰南两次与陈大远同志相见,从他的讲述中,才更详细地了解到父亲生前在《救国报》工作以及牺牲的情况。这以后,他寄给我一本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编的《新闻史料》,上面刊有他写的回忆录《记冀东〈救国报〉的几位烈士》,文中记述了四位《救国报》烈士,我父亲寒潮就在其中。还有一期《冀东文艺》,刊有他写的《高飞吧,年轻的一代》,较详细记述了他与我父亲相识和共同战斗的往事,以及我父亲牺牲的经过。
在这里,我将其中一些段落摘录如下,谨以此作为对《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长文的回响,以及表达对我父亲那一辈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坚定信仰的崇高敬意。
陈大远在《忆冀东〈救国报〉的几位烈士》一文中写道:
寒潮同志,河北丰润人,原名马建廷,化名文生、字辰,后改名寒潮 。从1941年《救国报》社迁到鲁家峪时开始,他就是报社的总务科长。报社的后勤工作,像财务、总务、生活物资的供应、隐蔽地洞的建造,住地的踏看选择等等,都由他来担任。但是,他的最繁难的工作、最艰巨的任务,并不是这些,而是要保证报纸、书刊编辑出版所需要的物资供应,像纸张、油墨、蜡纸、誊写印刷用具等等,是一日不可或缺的。
这些物资,游击区根据地是没有的,必须从敌人据点里购买运送出来,比较小的据点如县城,也是很难买到的,要到大据点,主要是天津、唐山等城市才能得到这些物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寒潮同志物色了许多住在游击区同敌据点有关系的人,并且通过这些人同敌据点里有办法、有爱国心的人士相交结,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报社需要的物资买到手,运到根据地。这样的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不管敌人制造多少障碍,不管在敌人封锁、“扫荡”多么紧张的时刻,在寒潮同志的艰苦奋斗之下,《救国报》所需要的物资,从来没中断过,总是保证充足的供应。
陈大远在《高飞吧,年轻的一代》一文中写道:
1941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走进了遵化县鲁家峪东河沟的一个院落,这是我第一次踏进革命工作的门槛。接待我的是《救国报》社社长崔林和寒潮同志。
我第一次踏进革命之门,在革命阵营里过第一个夜晚,就是同寒潮同志一起度过的。那一夜,我心情自然是不平静的,所以合不上眼,寒潮同志就陪我到能够合眼入睡的时候。
在这一夜里,我了解到,寒潮同志是丰润县小峪村人,自幼家境贫困,不得不到外边去当学徒、寻找职业,所以他并不是个道地的农民。他在镇上当过刻字工人,刻图章不仅要会操刀,而且要会执笔,真草隶篆,都要写得清楚匀整。他还做过石印工人,不但能掌握石印技术,而且写一笔很好的蝇头小楷。因此,我惊叹他是个文武全才的人。他的工作,需要很好的脚力,今天在鲁家峪,明天可能到丰润城外,后天可能到唐山近郊,甚至要到天津附近的关系地,然后再到若干存放印刷物资的基地,妥善地把物资坚壁起来。他的一身好拳脚,武生式的身板,帮助了他的工作。他的文才,就使他十分热爱报纸的印刷出版事业。
第二天,崔林和寒潮同志,把我送到山东耍儿峪,这儿有一个刻字小组,我就成了这个小组的成员。据说,寒潮同志经常到这儿来,以便了解誊写印刷物资的消耗情况。以后我们到鲁家峪以西的榛子峪、井儿峪一带活动,寒潮同志也经常在这里。不久之后,我们奉命把工作、宿营地点定在鲁家峪北峪,寒潮同志也经常在这里办公。
我们发现寒潮同志有一个极大特点,需要的时候,总是不顾个人,经受疲劳,承担风险,去解除同志和乡亲们的困苦和危难。有的同志说:“寒湖同志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极其反对这种说法,总是正颜厉色的给予反驳:“谁看见我在肋巴骨上插着两把尖刀的?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绿林好汉。”寒潮同志越认真,就越有点像窦尔墩再世的气概,大家越爱同他开玩笑。
有些同志说,寒潮的腿,像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他的心,像铸弹炉里的一团烈火,这团火不但炼着他自己,也炼着同他在一起的别人,使他们从朽铁变成一颗炸弹。
1944年初夏,青纱帐刚起。这时,寒潮同志为了从唐山运出一批印刷物资,同他的唯一助手张西庆同志,南下老庄子一带。
一天清晨,附近据点的敌人对寒潮同志住的村子实行包围、进攻,当他们发现这个突然情况的时候,敌人已经进院搜索,不可能突围转移了。摆在他们眼前的任务就是战斗。他们只有两个人,二把德枪,敌人几十倍于他们。他们研究了这个情况,决定一个人把住窗口,一个人把住门口,沉着应战,使有限的子弹,消灭更多的敌人。他们给敌人以足够的惩罚之后,英勇地牺牲在这里了。
关于他们战斗和牺牲的情况,只是后来听当地老乡说的。最了解情况的老乡也不是目击者,而是从现场,从敌人死亡情况,从寒潮和张西庆同志牺牲后的形态推断出来的。所以我不可能多置一句形容词。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悼念一位烈士是不用眼泪的,因为烈士最不喜欢眼泪。我同寒潮同志有些特殊关系,我第一天踏进革命之门,是他和崔林同志接待了我,我十分崇敬他的性格和品德,在危险的情况下,我同他共同行动过两三次,而最重要的,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他和崔林同志把我引进到党内。因此,当我听说他牺牲的时候,偷偷地哭了一场,我哭他,也替他的父亲、爱人和孩子们哭他。因为这时候,他们还不可能知道寒潮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也曾为他作了一首挽诗,当时不敢给人看,现在不妨抄在这里。
革命途程远未终,奈何君死我偏生?
英雄常共崎岖路,偷问苍天泪雨零。
寒潮同志牺牲两年多之后,也就是日本投降后的不久,我到他家去了一趟,想给他的家属一些安慰。谁知这次见面的情况出我意料之外。寒潮同志的父亲向我说,要打仗就得有牺牲,怕牺牲还当石印工人不好?他死的硬气,没给中国人和我们马家丢脸就好。这话出自一个失掉儿子的老人,是多么可贵呀!他的爱人也说,告诉报社领导,不要惦记我们,建廷一死,可能给家里留下一点困难,可是我们会克服的。不是我来安慰他们,而是他们在安慰我。我的眼泪憋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1983和1984年,陈大远同志还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讲述了他老伴在战争年代曾到我家养伤等事,情感真切。在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你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同志。尤其是我和他有特殊的友谊,并不言过其实。当然,这不只是私人感情,主要的还是阶级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北京有好几个同志都是你父亲的老战友。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要谈起你父亲和别的烈士的事情。你父亲在老同志们的心里是永远活着的。
你父亲的化名,第一次叫“文生”,1942年改为“宇辰”,1942年末改为“寒潮”(不是韩潮),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牺牲。这个名字基本上是他自起的,他原想叫“寒流”,后有政治部一位同志建议,“流”字不好,“潮”字更好,所以就叫作“寒潮”了。他在救国报社任总务科长,后来改为石印的印刷所长。因为你父亲有石印技术,还会刻图章。在工作上,他总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和同志的关系极好。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入党我不知道。但是我入党时你父亲是我的介绍人之一。
你父亲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他的工作,他的牺牲,对共产党员的称号是毫无愧色的。我一想起你父亲,总是以有这样一位老战友而自豪。
……
往事悠悠,并不如烟。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抗战烽火中这段可歌可泣的艰苦岁月,我们会永远铭记;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乃至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将永远鼓舞我们在新时代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