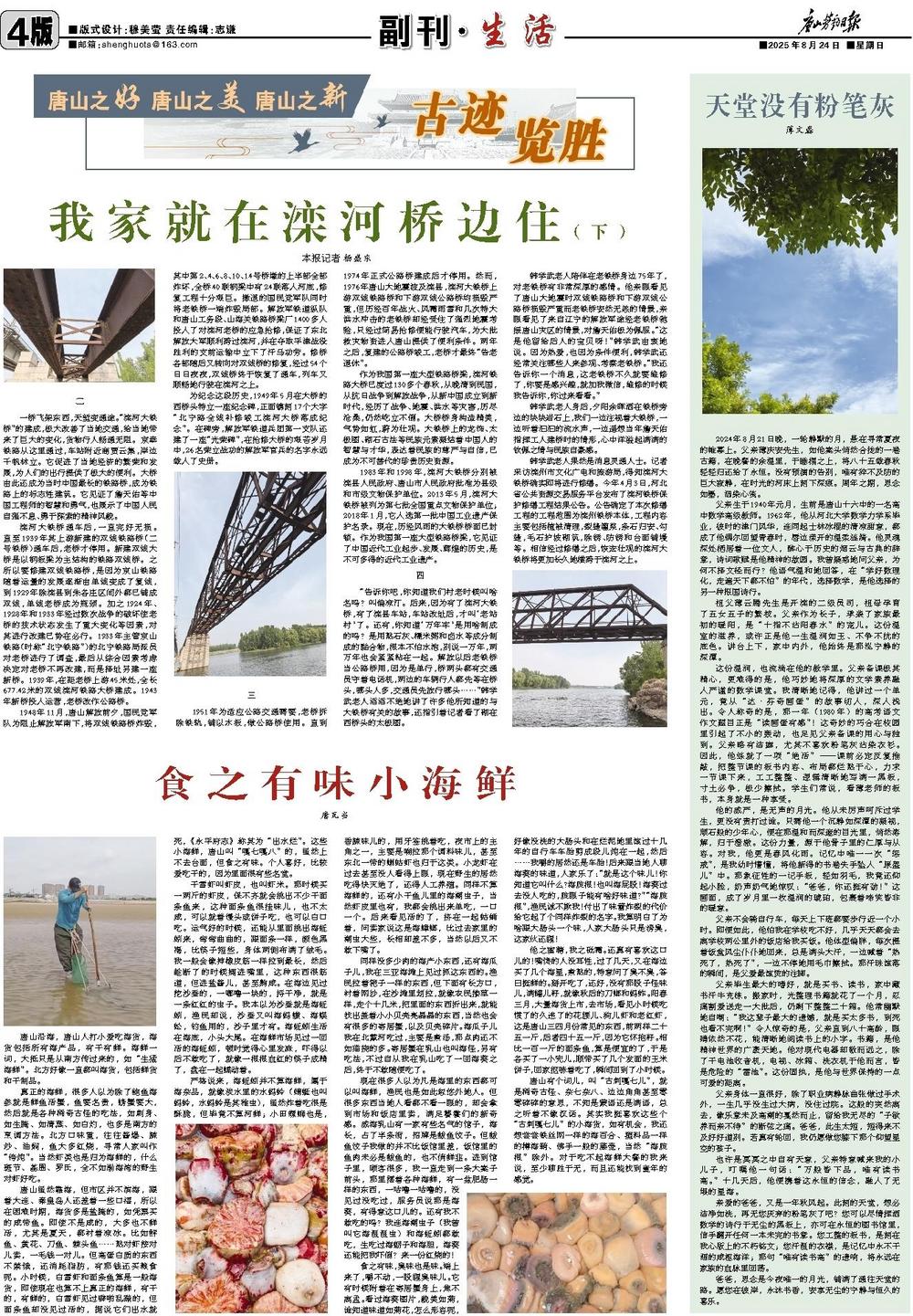2024年8月21日晚,一轮静默的月,悬在寻常夏夜的帷幕上。父亲薄庆安先生,如他案头悄然合拢的一卷古籍,在晚餐的余温里,于睡榻之上,将八十五载春秋轻轻归还给了永恒。没有预演的告别,唯有猝不及防的巨大寂静,在时光的河床上刻下深痕。周年之期,思念如墨,洇染心笺。
父亲生于1940年元月,生前是唐山十六中的一名高中数学高级教师。1962年,他从河北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彼时的津门风华,连同起士林冰棍的清凉甜意,都成了他偶尔回望青春时,唇边漾开的温柔涟漪。他灵魂深处栖居着一位文人,醉心于历史的烟云与古典的辞章,诗词歌赋是他精神的故园。我曾疑惑地问父亲,为何不择文径而行?他语气温和地回答,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选择数学,是他选择的另一种报国诗行。
祖父薄云腾先生是开滦的二级员司,祖母孕育了五女五子的繁枝。父亲作为长子,承袭了家族最初的暖阳,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宠儿。这份温室的滋养,或许正是他一生温润如玉、不争不扰的底色。讲台上下,家中内外,他始终是那泓宁静的深潭。
这份温润,也流淌在他的教学里。父亲备课极其精心,更难得的是,他巧妙地将深厚的文学素养融入严谨的数学课堂。我清晰地记得,他讲过一个单元,竟从“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切入,深入浅出。令人称奇的是,那一年(1980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正是“读画蛋有感”!这奇妙的巧合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足见父亲备课的用心与独到。父亲略有洁癖,尤其不喜欢粉笔灰沾染衣衫。因此,他练就了一项“绝活”——课前必定反复推敲,把整节课的板书内容、布局都烂熟于心,力求一节课下来,工工整整、逻辑清晰地写满一黑板,寸土必争,极少擦拭。学生们常说,看薄老师的板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他的威严,是无声的月光。他从未厉声呵斥过学生,更没有责打过谁。只需他一个沉静如深潭的凝视,顽石般的少年心,便在那温和而深邃的目光里,悄然溶解,归于澄澈。这份力量,源于他骨子里的仁厚与从容。对我,他更是春风化雨。记忆中唯一一次“惩戒”,是我幼时懵懂,将他新得的书卷失手坠入“尿盔儿”中。那象征性的一记手板,轻如羽毛,我竟还仰起小脸,奶声奶气地惊叹:“爸爸,你还挺有劲!”这画面,成了岁月里一枚温润的琥珀,包裹着啼笑皆非的暖意。
父亲不会骑自行车,每天上下班都要步行近一个小时。即便如此,他怕我在学校吃不好,几乎天天都会去离学校两公里外的饭店给我买饭。他体型偏胖,每次提着饭盒风尘仆仆地回来,总是满头大汗,一边喊着“热死了,热死了”,一边不停地用毛巾擦拭。那汗珠滚落的瞬间,是父爱最滚烫的注脚。
父亲毕生最大的嗜好,就是买书、读书,家中藏书汗牛充栋。搬家时,光整理书籍就花了一个月,忍痛割爱送走一大批后,仍剩下整整二十箱。他常幽默地自嘲:“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买太多书,到死也看不完啊!”令人惊奇的是,父亲直到八十高龄,眼睛依然不花,能清晰地阅读书上的小字。书籍,是他精神世界的广袤天地。他对现代电器却敬而远之,除了干电池收音机,电视、冰箱、洗衣机于他而言,皆是危险的“雷池”。这份固执,是他与世界保持的一点可爱的距离。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除了职业病静脉曲张做过手术外,一生几乎没生过大病,没住过院。这般的突然离去,像乐章未及高潮的戛然而止,留给我无尽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断弦之痛。爸爸,此生太短,短得来不及好好道别。若真有轮回,我仍愿做您膝下那个仰望星空的孩子。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父亲特意喊来我的小儿子,叮嘱他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几天后,他便携着这永恒的信念,融入了无垠的星海。
亲爱的爸爸,又是一年秋风起。此刻的天堂,想必洁净如洗,再无您厌弃的粉笔灰了吧?您可以尽情挥洒数学的诗行于无尘的黑板上,亦可在永恒的图书馆里,信手翻开任何一本未完的书章。您工整的板书,是刻在我心版上的不朽铭文;您汗湿的衣襟,是记忆中永不干涸的咸涩海洋;那句“唯有读书高”的遗响,将永远在家族的血脉里回荡。
爸爸,思念是今夜唯一的月光,铺满了通往天堂的路。愿您在彼岸,永沐书香,安享无尘的宁静与恒久的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