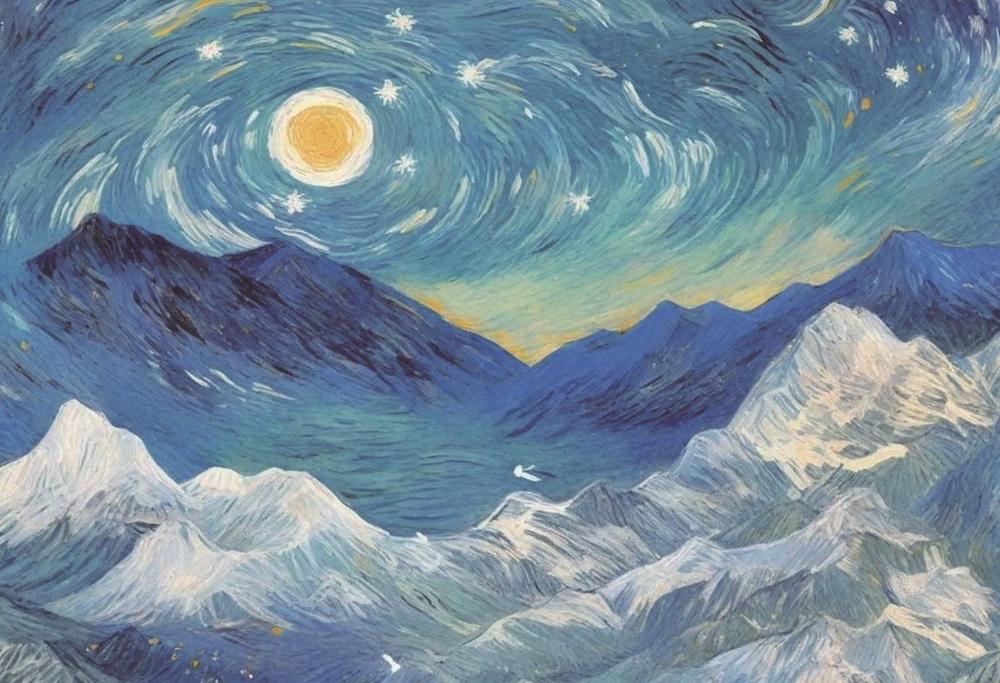时光荏苒,转眼恩师唐向荣已离开整整十三载。铺纸提笔,他的音容笑貌恍若眼前,学习工作的许多过往便盈满脑际。
初遇恩师
我是在滦县二中完成的高中学业。1985年秋季开学,我们进入高二上学期,高一的语文老师要陪师母去北京看病,我们的语文课就分别由两个老师来担任,基础部分秦学俊老师代课,作文部分唐向荣老师来教。
印象很深,老师上作文课,不是直接布置作文题目,而是先读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从生活中的小事引申出耐人寻味的道理,然后再讲写作要领。至今还记得老师文中讲的两个小故事。其一是说他袄兜儿里装着些瓜子,边走边嗑,吃到最后,从袄兜底部抠出最后一个扔到嘴里,嗑完一嚼,原来是个臭的。我们听得哄堂大笑,接下来他就讲习惯性思维的弊端和功亏一篑的道理。其二是说一家人盖房子,在上边垒墙的泥瓦匠冲着下边递砖的人喊:“照着我的脑袋扔!”那人是新手,怕砸伤了他,就照着他腰的位置扔上去,结果上边人没接到,砖落下来。泥瓦匠又大声喊:“照着我的脑袋扔!”下边人真的使个大劲,砖朝泥瓦匠的脑袋飞去,泥瓦匠一伸手,接个正着,说“这就对喽。”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随后的论述让我们明白了“取之乎上,得乎其中,取之乎中,得乎其下”的哲理。
还有,布置的作文写完交上去,并不算完成作业。老师会逐篇批改,提出修改意见,同学们再重新写。记得我的一篇作文《不珍惜时间是最大的浪费》前后修改了四次。对记叙文,老师有十项对照标准:中心是否明确,六大要素全不全,有无环境描写,是否写出了真情实感,有没有独特的角度,详略是否得当,结构是否完整,有无错别字,有无病句,书写是否规范。当年的一篇《自我修改对照手记》详细记录下这些内容。
有意思的是,当时老师教我们高二四班和隔壁的高二三班,他会定期组织两个班的同学互批作文。就是将两个班的作文本进行交换,发到同学手中,拿到谁的作文,就认真阅读,从标点符号到文章结构,从好的段落句子到不足之处,都要标注,然后再写一篇完整的评论或体会,有的同学写的评论比原文还要长。老师再对作文和评论一一进行评改,如果哪点评论能得到老师认可心里会高兴一个礼拜。那段时间,两个班的同学见面都会互相聊聊作文的事儿,说说对方班里谁的作文写得好。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周老师让我们选身边事就事论理写一篇作文。三班一女同学文中写道“听说二中有个图书馆,可我们连个书毛都没见过”,老师向学校反映了同学意见,于是学校图书馆向同学开放,小说杂志就到了大家手里,上课偷着看,回宿舍猫被窝看,一时间好不过瘾。可是好景不长,我们班董富同学写一篇《凡事应有度》,列举了我们贪恋课外读物的种种,于是,图书馆又关闭了。直到毕业后我们师生见面,此事还是笑谈。
临近期末的一节作文课,老师站到讲台,说:“快一个学期了,同学们一直在听我说,听我讲,现在我提个建议,咱们下周的作文课,就来一场作文讲演会,同学们站到讲台上,可以讲自己的作文,也可以讲同学的作文,展示一下咱们半年的学习成果,大家说好不好?”“好!好!”同学们鼓掌欢呼。经过一个星期的报名准备,作文讲演会如期举行。一进课堂,老师用双勾字在黑板上写下“作文讲演会”五个大字,并涂成红色,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还是老师先开场,讲演他写的《八十年代青年的气度和襟怀》,然后有十几个同学陆续上台。第一次演讲,难免紧张和兴奋,但热烈又活泼的氛围,让没有报名的同学后来也走上了讲台……作文课上成讲演会,这是我们心中美好的记忆。
翻开老箱底,当年的作文本保存完好。半年时光,50页的本子,每页300字,竟然写满了正反两面。发黄的纸张、稚嫩的文笔,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后来才知道,老师给我们上课期间,他正在进行“以文教文,以文引文”的语文教改,我们恰逢其时。
高二上学期,有幸遇恩师。
难忘十年
高中时就知道老师在研究辛亥滦州起义,没想到后来竟有幸调入滦县政协,在老师手下工作10年。不仅对滦州起义史实有了深入了解,对老师的治学精神更是心存敬意。
1911年在滦州发生的辛亥滦州起义,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策划的一场武装反清起义,是武昌起义“最得力之应援”,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1936年颁布的《国民政府令》予以高度评价:“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
老师于1960年开始接触滦州起义课题。当时他正在滦县一中上高中,经常作为青年代表参加县里的一些文化工作会议,结识了原县志编修吴湘浦先生和原县志总修张凤翔先生。两位老先生见老师对地方史研究有浓厚兴趣,就将他们所知滦州起义的事情全部相告,老师听了很是震惊,又觉这是发生在故土的重大事件,边听边问边做记录,此后经常跟两位老先生探讨相关内容。两位老先生因年事已高未完成的研究,终遇可托之人。吴老曾为老师写出千字提纲,张老将他珍藏半个世纪的起义文告、《纪念特刊》《荣哀录》残稿等郑重交给老师并多所嘱咐,不久二老便相继辞世。
受此重托,老师遂下决心搜罗史籍,探访遗址,几经坎坷,初衷未改。1988年调入县政协文史办,全力以赴投入辛亥滦州起义课题研究之中。1991年7月,老师的书稿《辛亥滦州起义》作为《滦县文史资料》第七集完成内部刊印,课题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从不迷信的他,在一个肃静的夜晚,在办公楼的墙角,将一本还散着墨香的《辛亥滦州起义》一页页撕开,一页页点燃,向吴湘浦、张凤翔两位老先生深深鞠躬,汇报多年的研究历程,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老师说,这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书稿刊印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老师认为,应让海内外了解史实,让辛亥滦州起义课题得到学术界认可,最后应该在起义故地建祠立碑,让志士后人有凭吊之所。老师的建议得到当时县委、县政协领导的认可并达成共识,于1992年在县政协成立滦县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
参加工作后,常从老师这儿带些资料回去整理。为此,受老师推荐,我于1992年9月调入研究会。研究会办公室在政协三楼,同事宿强先我到岗。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在顶层四楼。
工作正式铺开,老师让我们从誊抄资料入手。他的办公室东西两墙的书橱里、木架上分门别类摆满各种书籍资料,在不同的页码夹着做了记号的小纸条。报架上挂着用铁夹子夹着的待复信函和各种通知文件。老师从中拿出部分资料交给我们,说明抄写内容,要求300字稿纸要用复写纸一式两份,笔迹要清楚工整,让我们边抄边熟悉资料,并嘱咐这抄抄写写的工作会比较枯燥,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抄完一摞,再到他那换新的任务。遇到来自台湾和海外的资料,都是繁体字,需抄成简体,我们就不断翻字典,真是有些像小学生。老师到三楼看到后,就说:“你们不妨把查过的繁体字和对应的简体字做成对照卡片。”照做之后抄写效率明显提高,那些陌生的繁体字也变得熟悉起来,当年积累的几沓对照卡片保存至今。
到研究会之后才知道,多年做学术研究工作,老师已养成每天三点必起的习惯,他说那个时候脑筋思路最清晰,他的大多数史学考辨文章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那天刚上班,老师到三楼办公室,见宿强我俩就笑着说:“今天你们差点看不到我喽。”原来,他三点起来,先到办公室外凉台的围墙坐了一会儿,恍惚间,以为坐在椅子上,就想往后靠,一闪身突然就清醒过来。我俩听得惊出一身冷汗,老师却说:“任务没完成,阎王不收留呀。”
老师所说没完成的任务,就是研究会成立后要做的很多事情。
接下来的两三年间,同事宿强调走,郭清、陈运生相继到来。老师的学术研究文章在《团结报》《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刊物《辛亥革命研究》发《辛亥北方革命专刊》,收录老师的《论孙中山的北方革命观》《论李大钊与辛亥北方革命的关系》等重要论述,老师的学术观点引起学术界关注。
对三个年轻人,老师常让我们为他写的文章挑毛病,开始我们不敢,心想也挑不出来。老师就鼓励说:“我又不是圣人,写的东西肯定有毛病,你们细心看,肯定能找出来。”于是我们静下心来边看边学,熟知了有关学术观点,再挑些标点呀、措辞呀之类的“毛病”,老师很高兴,说“有你们把关,文章寄出去心里就有底喽。”其实我们何尝不知老师的良苦用心呀,他是在教我们做学问的方法,让我们坐得住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老师做学问的信条。
最难忘是1995年。经过紧张筹备,7月25日至27日,河北省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25日的成立大会上,滦县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升格为河北省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这是辛亥滦州起义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26日至27日,辛亥滦州起义研讨会在滦州宾馆举行,看过文献资料片《辛亥滦州起义》后,老师介绍研究历程,接下来就孙中山、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的关系同与会专家学者展开研讨,专家提出疑问,老师现场作答,由于这是当时史学界的新论点,老师又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史研究者,气氛紧张又热烈。为留下专家们的宝贵意见,老师事先安排做好全程录音。
两会结束,“河北省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的牌匾郑重挂到县政协办公楼前厅外,《团结报》《光明日报》和省市县新闻媒体相继报道大会消息,辛亥滦州起义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只是这个新阶段的开始有点出乎意料。我们还沉浸在会后的喜悦之中,开始整理大会留下的各种资料,一个声音就扑面而来,“老唐的观点被专家否了。”接下来就有热心人士或来办公室或打电话问询此事。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老师告诉我们“别着急,先整理研讨会的录音资料,把专家们现场的提问捋到一起。”我们三个年轻人分头对录音带反复聆听,并整理成文字,最后梳理出14个问题,并没发现否定老师观点的言论,其中有些问题我们三个都能回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老师反而很淡定,说:“做研究不是小姑娘跳舞,处处都要有掌声。我们心中无愧,至于其他人,理解万岁,不理解也万岁。”我想这应该是老师多年坐冷板凳的深刻体会。
之后陈运生调走,2001年老师退休但仍坚持工作。2002年全县机构改革,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与县委党史研究室合署办公,郭清调政协宣教科,我调到县委党史研究室,老师回家。
十年时光,随恩师工作,得恩师教诲,受益终生。
回家后的老师并未放下辛亥滦州起义研究及相关工作。继续推进重要课题,在电视台举办专题讲座,进校园、进机关宣讲革命历史……古稀之年还曾去台湾参加相关学术研讨会,辛亥滦州起义研究已深深融入老师的血脉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