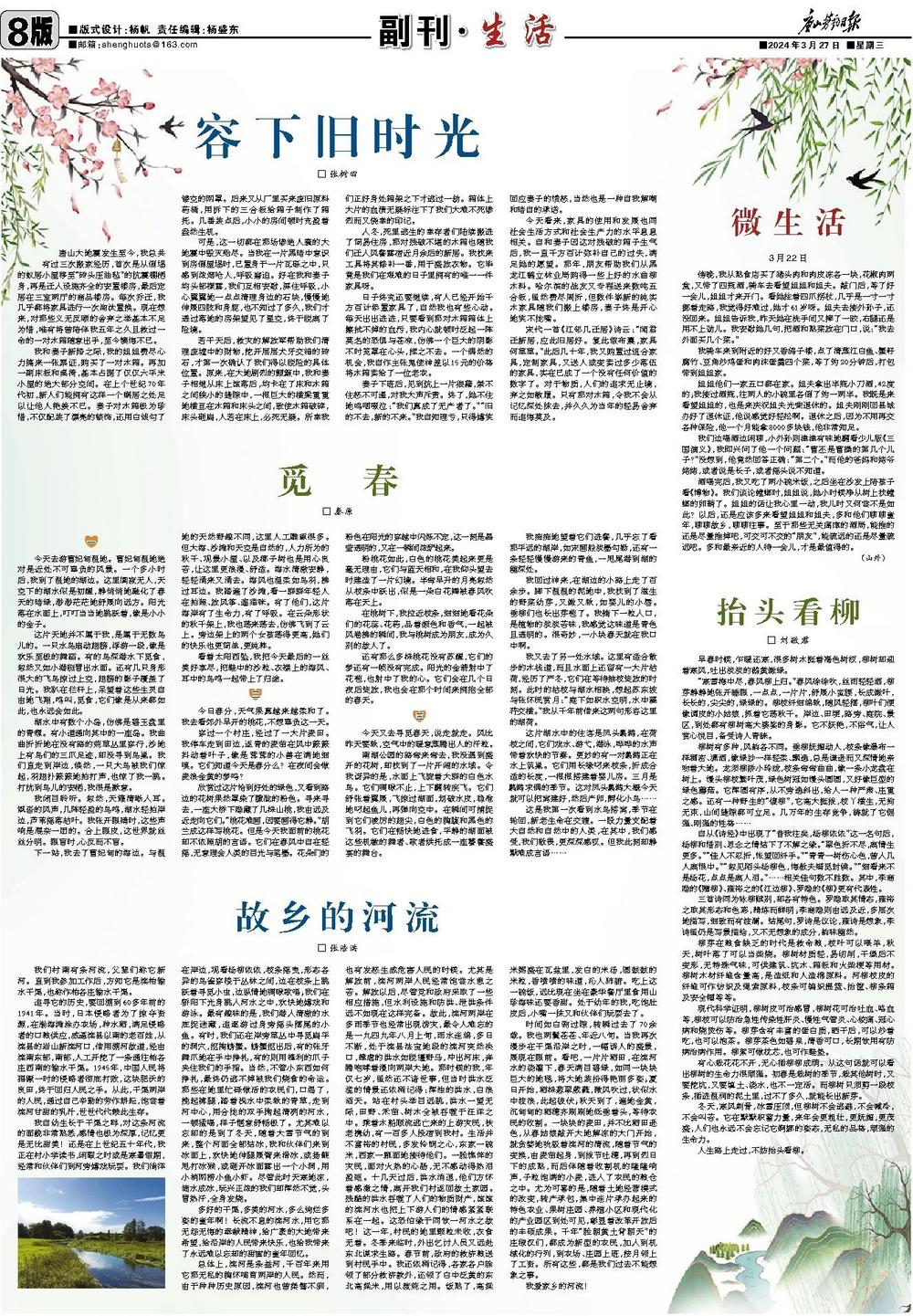唐山大地震发生至今,我总共有过三次搬家经历,首次是从倒塌的蚁居小屋移至“砖头压油毡”的抗震棚栖身,再是迁入设施齐全的安置楼房,最后定居在三室两厅的商品楼房。每次乔迁,我几乎都将家具进行一次淘汰置换。现在想来,对那些义无反顾的舍弃之举基本不足为惜,唯有将曾陪伴我五年之久且救过一命的一对木箱随意出手,至今懊悔不已。
我和妻子新婚之际,我的姐姐费尽心力搞来一张票证,购买了一对木箱。再加一副床板和桌椅,基本占据了仅仅六平米小屋的绝大部分空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新人们能拥有这样一个蜗居之处足以让他人艳羡不已。妻子对木箱极为珍惜,不仅配装了漂亮的锁饰,还用白线勾了镂空的网罩。后来又从厂里买来废旧原料药桶,用拆下的三合板给箱子制作了箱托。几番装点后,小小的房间顿时充盈着盎然生机。
可是,这一切都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中毁灭殆尽。当我在一片黑暗中意识到房倒屋塌时,已置身于一片瓦砾之中,只感到浓烟呛人,呼吸窘迫。好在我和妻子均头部裸露,我们互相安慰,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清理身边的石块,慢慢地伸展四肢和身躯,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透过落地的房架望见了星空,终于脱离了险境。
若干天后,救灾的解放军帮助我们清理废墟中的财物,挖开层层犬牙交错的砖石,才第一次确认了我们得以脱险的具体位置。原来,在大地剧烈的颠簸中,我和妻子相继从床上滚落后,均卡在了床和木箱之间狭小的缝隙中,一根巨大的横梁重重地横亘在木箱和床头之间,致使木箱破碎,床头砸扁,人若在床上,必死无疑。所幸我们正好身处箱架之下才逃过一劫。箱体上大片的血渍无疑标注下了我们大难不死惨烈而又侥幸的印记。
入冬,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们陆续搬进了简易住房,那对残破不堪的木箱也随我们迁入风餐露宿近月余后的新居。我找来工具将其修补一番,用于盛放衣物。它毕竟是我们在艰难的日子里拥有的唯一一件家具呀。
日子终究还要继续,有人已经开始千方百计添置家具了,自然我也有些心动。每天出出进进,只要看到那对木箱箱体上擦拭不掉的血污,我内心就顿时泛起一阵莫名的恐惧与苍凉,仿佛一个巨大的阴影不时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自作主张鬼使神差以15元的价格将木箱卖给了一位老农。
妻子下班后,见到炕上一片狼藉,禁不住怒不可遏,对我大声斥责。终了,她不住地呜咽啜泣:“我们真成了无产者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自知理亏,只得嬉笑回应妻子的愤怒,当然也是一种自我解嘲和暗自的承诺。
今天看来,家具的使用和发展也同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息息相关。自和妻子因这对残破的箱子生气后,我一直千方百计弥补自己的过失,满足她的愿望。那年,朋友帮助我们从黑龙江鹤立林业局购得一些上好的水曲柳木料。哈尔滨的战友又专程送来数吨五合板,虽然费尽周折,但数件崭新的纯实木家具随我们搬上楼房,妻子终是开心地笑不拢嘴。
宋代一首《江邻几迁居》诗云:“闻君迁新居,应此旧居好。复此假布囊,家具何草草。”此后几十年,我又购置过组合家具,定制家具,又送人或变卖过多少落伍的家具,实在已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数字了。对于物质,人们的追求无止境,弃之如敝履。只有那对木箱,令我不会从记忆深处抹去,并久久为当年的轻易舍弃而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