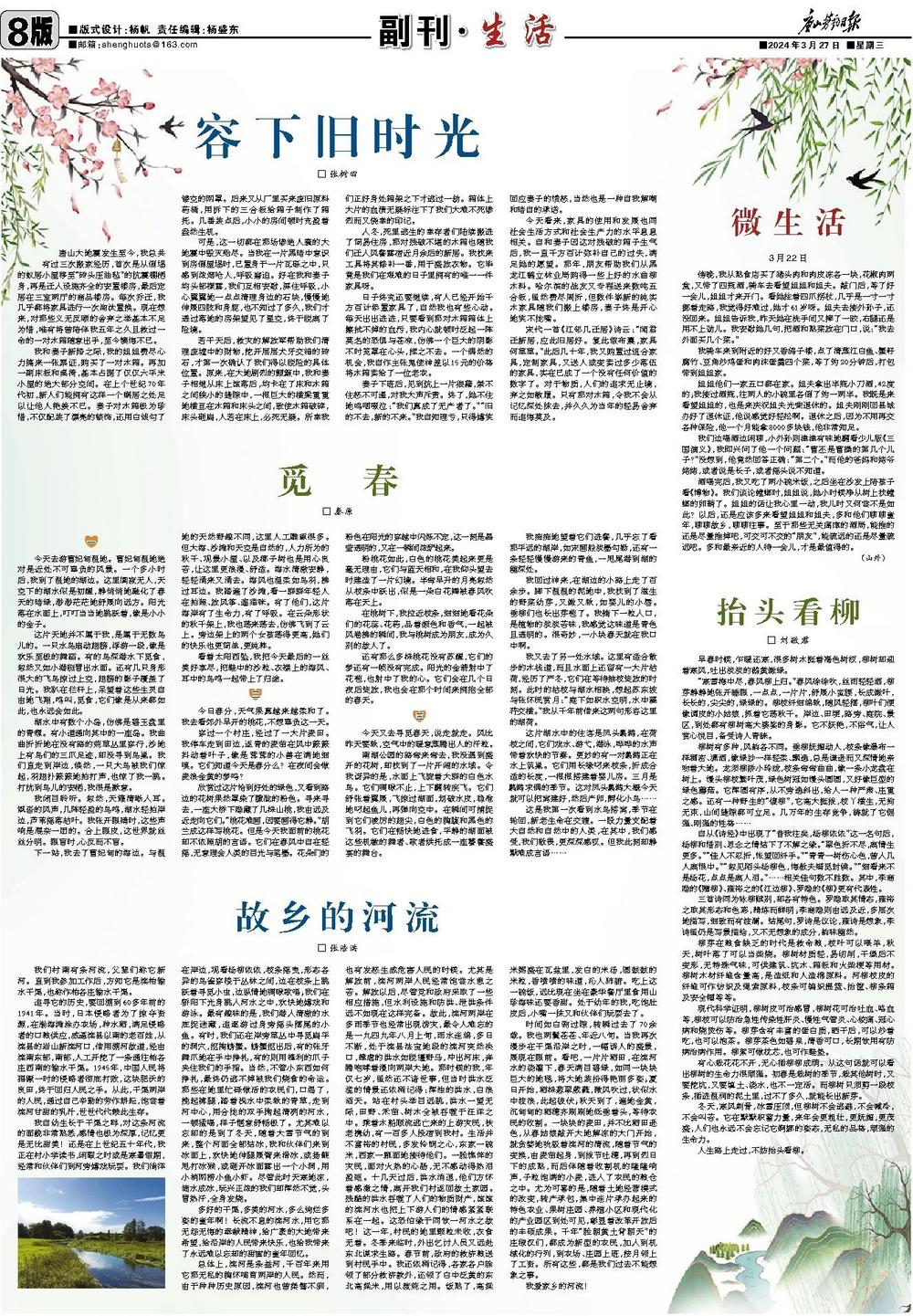我们村南有条河流,父辈们称它新河。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方知它是滦柏输水干渠,也称作柏各庄输水干渠。
追寻它的历史,要回溯到60多年前的1941年。当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资源,在渤海滩涂办农场,种水稻,满足侵略者的口粮供应,威逼滦县以南的老百姓,从滦县的岩山新滦河口,借用溯河故道,经由滦南东部,南部,人工开挖了一条通往柏各庄西南的输水干渠。1945年,中国人民将猖獗一时的侵略者彻底打败,这块肥沃的良田,终于回归人民之手。从此,干渠两岸的人民,通过自己辛勤的劳作耕耘,饱尝着滦河甘甜的乳汁,世世代代赖此生存。
我自幼生长于干渠之畔,对这条河流的面貌非常熟悉,感情也极为深厚,记忆更是无比甜美!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正在村小学读书,闲暇之时或是寒暑假期,经常和伙伴们到河旁嬉戏玩耍。我们徜徉在岸边,观看杨柳依依,枝条摇曳,形态各异的鸟雀穿梭于丛林之间,边在枝条上跳跃着寻觅小虫,边纵情地啁啾歌唱;我们在骄阳下光身跳入河水之中,欢快地嬉戏和游泳。最有趣味的是,我们潜入清澈的水底捉迷藏,追逐游过身旁摇头摆尾的小鱼。有时,我们还在岸旁草丛中寻觅扁平的洞穴,抠掏螃蟹。螃蟹抠出后,有的张牙舞爪地在手中挣扎,有的则用锋利的爪子夹住我们的手指。当然,不管小东西如何挣扎,最终仍逃不掉被我们烧食的命运。那些在地里忙碌做活的农民们,口渴了,挽起裤腿,踏着浅水中柔软的青草,走到河中心,用合拢的双手掬起清冽的河水,一顿猛喝,样子惬意舒畅极了。尤其难以忘却的是到了冬天,随着大雪节气的到来,整个河面全部结冰,我和伙伴们来到冰面上,欢快地伸腿展臂来滑冰,或扬鞭甩打冰猴,或砸开冰面露出一个小洞,用小梢网捞小鱼小虾。尽管此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玩兴正浓的我们却浑然不觉,头冒热汗,全身发烧。
多好的干渠,多美的河水,多么绚烂多姿的童年啊!长流不息的滦河水,用它那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给广袤的大地带来希望,给沿岸的人民带来快乐,也给我带来了永远难以忘却的甜蜜的童年回忆。
总体上,滦河是条益河,千百年来用它那无私的胸怀哺育两岸的人民。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滦河也曾桀骜不驯,也有发怒生威危害人民的时候。尤其是解放前,滦河两岸人民经常饱尝水患之苦。解放以后,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但水利设施和防洪、泄洪条件远不如现在这样完备。故此,滦河两岸在多雨季节也经常出现涝灾,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旬,雨水连绵,多日不断,处于滦县法宝地段的滦河突然决口,肆虐的洪水如脱缰野马,冲出河床,奔腾咆哮着漫向两岸大地。那时候的我,年仅七岁,虽然还不谙世事,但当时洪水泛滥的情景还依稀记得:浑浊的洪水,白浪滔天。站在村头举目远眺,洪水一望无际,田野、禾苗、树木全被吞噬于汪洋之中。乘着木船顺流逃亡来的上游灾民,扶老携幼,有一百多人投宿到我村。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多发怜悯之心,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瓢面地接待他们。一脸憔悴的灾民,面对火热的心肠,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十几天过后,洪水消退,他们方怀着感激之情,离开我们村返回故土家园。残酷的洪水吞噬了人们的物质财产,滚滚的滦河水也把上下游人们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恐怕缘于同饮一河水之故吧!这一年,村民的地里颗粒未收,衣食无着。冬季来临时,外出乞讨人员又远赴东北谋求生路。春节前,政府的救济粮送到村民手中。我还依稀记得,各家各户除领了部分救济款外,还领了白中泛黄的东北高粱米,用以渡荒之用。饭熟了,高粱米粥盛在瓦盆里,发白的米汤,圆鼓鼓的米粒,香喷喷的味道,沁人肺腑。吃上这一碗饭,远比现在坐在豪华餐厅里食用山珍海味还要香甜。处于幼年的我,吃饱肚皮后,小嘴一抹又和伙伴们玩耍去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过去了70余载。我也两鬓苍苍、年近八旬。当我再次漫步在干渠沿岸之时,一幅诱人的盛景,展现在眼前。看吧,一片片稻田,在滦河水的浇灌下,春天满目碧绿,如同一块块巨大的地毯,将大地装扮得艳丽多姿;夏日开始,稻株葱翠葳蕤,微风吹过,状似水中波浪,此起彼伏;秋天到了,遍地金黄,沉甸甸的稻穗齐刷刷地低垂着头,等待农民的收割。一块块的麦田,并不比稻田逊色,从春姑娘敲开大地解冻的大门开始,就贪婪地吮吸着滦河的清流,随着节气的变换,由麦苗起身,到拔节吐穗,再到烈日下的成熟,而后伴随着收割机的隆隆响声,子粒饱满的小麦,进入了农民的粮仓之中。尤为可喜的是,随着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转产承包,集中连片承办起来的特色农业、果树庄园、养殖小区和现代化的产业园区到处可见,彰显着改革开放后的丰硕成果。千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们,都成为新型的农民,加入到机械化的行列,到农场、庄园上班,按月领上了工资。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不能想象之事。
我爱家乡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