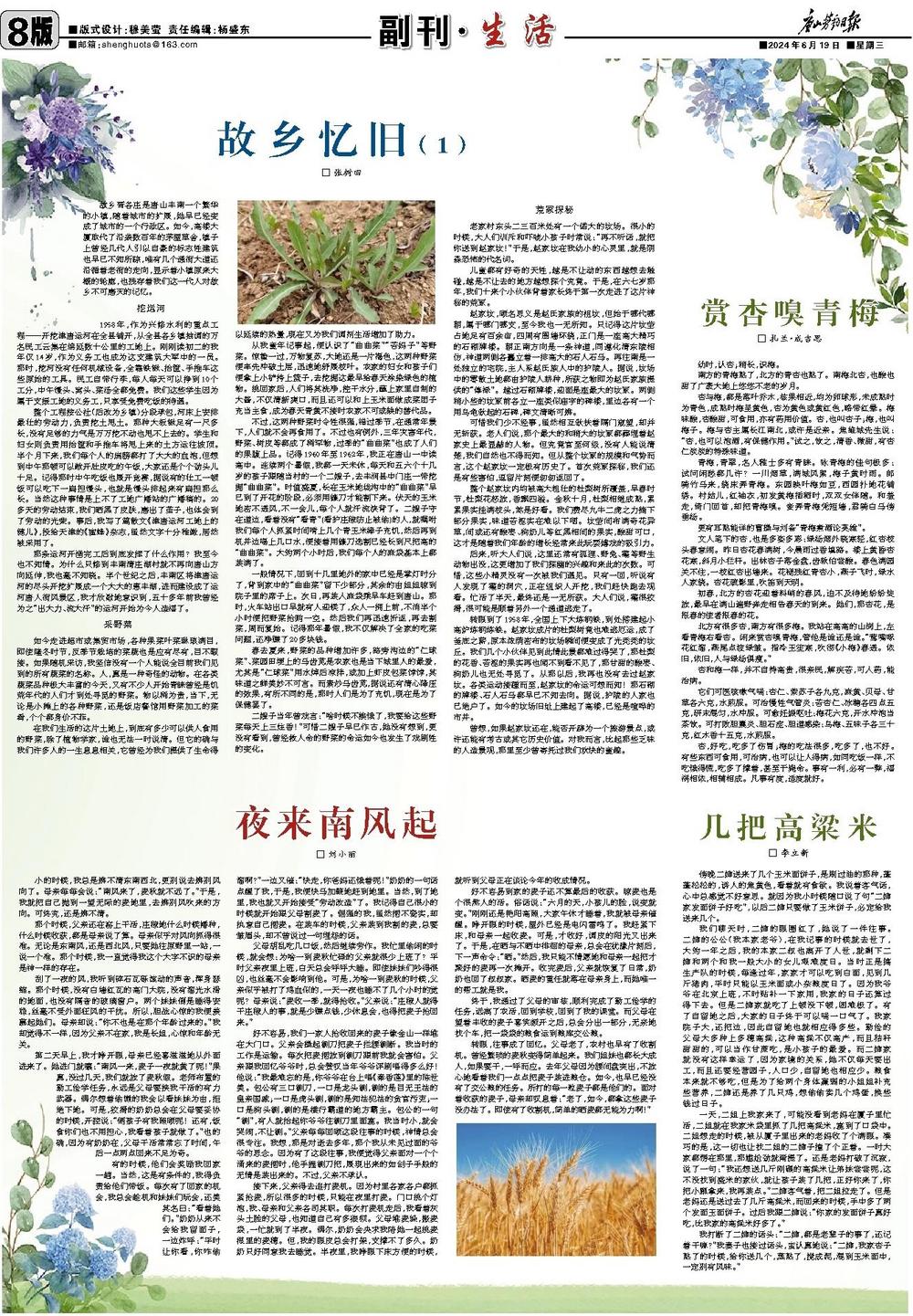故乡胥各庄是唐山丰南一个繁华的小镇,随着城市的扩展,她早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一个行政区。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沿袭数百年的茅屋草舍,镇子上曾经几代人引以自豪的标志性建筑也早已不知所踪,唯有几个通街大道还沿循着老街的走向,显示着小镇原来大概的轮廊,也残存着我们这一代人对故乡不可磨灭的记忆。
挖运河
1958年,作为兴修水利的重点工程——开挖津唐运河在全县铺开,从全县各乡镇抽调的万名民工云集在绵延数十公里的工地上。刚刚读初二的我年仅14岁,作为义务工也成为这支建筑大军中的一员。那时,挖河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铁锹、抬筐、手推车这些原始的工具。民工自带行李,每人每天可以挣到10个工分,中午馒头、窝头、菜汤全都免费。我们这些学生因为属于支援工地的义务工,只享受免费吃饭的待遇。
整个工程按公社(后改为乡镇)分段承包,河床上安排最壮的劳动力,负责挖土甩土。那种大板锹足有一尺多长,没有足够的力气是万万挖不动也甩不上去的。学生和妇女则负责用抬筐和手推车将甩上来的土方运往坡顶。半个月下来,我们每个人的肩膀都打了大大的血泡,但想到中午那顿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午饭,大家还是个个劲头儿十足。记得那时中午吃饭也展开竞赛,据说有的壮工一顿饭可以吃下一扁担馒头,也就是馒头排起来有扁担那么长。当然这种事情是上不了工地广播站的广播稿的。20多天的劳动结束,我们晒黑了皮肤,磨出了茧子,也体会到了劳动的光荣。事后,我写了篇散文《津唐运河工地上的健儿》,投给天津的《蜜蜂》杂志,虽然文字十分稚嫩,居然被采用了。
那条运河开凿完工后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我至今也不知情。为什么只修到丰南清庄湖村就不再向唐山方向延伸,我也毫不知晓。半个世纪之后,丰南区将津唐运河的尽头开挖扩展成一个大大的惠丰湖,进而建设成了运河唐人街风景区,我才欣慰地意识到,五十多年前我曾经为之“出大力、流大汗”的运河开始为今人造福了。
采野菜
如今走进超市或集贸市场,各种果菜叶菜琳琅满目,即使隆冬时节,反季节栽培的菜蔬也是应有尽有,目不暇接。如果随机采访,我坚信没有一个人能说全目前我们见到的所有蔬菜的名称。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各类蔬菜品种极大丰富的今天,又有不少人开始青睐曾经是饥荒年代的人们才到处寻觅的野菜。物以稀为贵,当下,无论是小摊上的各种野菜,还是饭店餐馆用野菜加工的菜肴,个个都身价不菲。
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到底有多少可以供人食用的野菜,除了植物学家,谁也无法一时说清。但它的确与我们许多人的一生息息相关,它曾经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得以延续的热量,现在又为我们调剂生活增加了助力。
从我童年记事起,便认识了“曲曲菜”“苦妈子”等野菜。惊蛰一过,万物复苏,大地还是一片褐色,这两种野菜便率先冲破土层,迅速地舒展枝叶。农家的妇女和孩子们便拿上小铲挎上篮子,去挖掘这最早给春天涂染绿色的植物。挑回家后,人们将其洗净,控干水分,蘸上家里自制的大酱,不仅清新爽口,而且还可以和上玉米面做成菜团子充当主食,成为春天青黄不接时农家不可或缺的替代品。
不过,这两种野菜时令性很强,错过季节,在通常年景下,人们就不会再食用了。不过也有例外,三年灾害年代,野菜、树皮等都成了稀罕物,过季的“曲曲菜”也成了人们的果腹上品。记得1960年至1962年,我正在唐山一中读高中。连续两个暑假,我都一天未休,每天和五六个十几岁的孩子跟随当村的一个二嫂子,去丰润县中门庄一带挖掘“曲曲菜”。时值盛夏,长在玉米地垅沟中的“曲曲菜”早已到了开花的阶段,必须用镰刀才能割下来。伏天的玉米地密不透风,不一会儿,每个人就汗流浃背了。二嫂子守在道边,看着没有“看青”(看护庄稼防止被偷)的人,就嘱咐我们每个人抓紧时间啃上几个青玉米棒子充饥,然后再到机井边喝上几口水,便接着用镰刀选割已经长到尺把高的“曲曲菜”。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每个人的麻袋基本上都装满了。
一般情况下,回到十几里地外的家中已经是掌灯时分了,背到家中的“曲曲菜”留下少部分,其余的由姐姐晾到院子里的席子上。次日,再装入麻袋乘早车赶到唐山。那时,火车站出口早就有人迎候了,众人一拥上前,不消半个小时便把野菜抢购一空。然后我们再迅速折返,再去割菜,周而复始。记得那年暑假,我不仅解决了全家的吃菜问题,还净赚了20多块钱。
春去夏来,野菜的品种增加许多,路旁沟边的“仁球菜”、菜园田埂上的马齿苋是农家也是当下城里人的最爱,尤其是“仁球菜”用水焯后凉拌,或加上虾皮包菜饽饽,其味道之鲜美妙不可言。而素炒马齿苋,据说还有清心降压的效果,有所不同的是,那时人们是为了充饥,现在是为了保健罢了。
二嫂子当年曾戏言:“啥时候不挨饿了,我要给这些野菜每天上三炷香!”可惜二嫂子早已作古,她没有想到,更没有看到,曾经救人命的野菜的命运如今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荒冢探秘
老家村东头二三百米处有一个偌大的坟场。很小的时候,大人们训斥和吓唬小孩子时常说:“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赵家坟!”于是,赵家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是阴森恐怖的代名词。
儿童都有好奇的天性,越是不让动的东西越想去触碰,越是不让去的地方越想探个究竟。于是,在六七岁那年,我们十来个小伙伴背着家长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片神秘的荒冢。
赵家坟,顾名思义是赵氏家族的祖坟,但始于哪代哪朝,属于哪门哪支,至今我也一无所知。只记得这片坟茔占地足有百余亩,四周有围墙环绕,正门是一座高大精巧的石砌牌楼。朝正南方向是一条神道,同遵化清东陵相仿,神道两侧各矗立着一排高大的石人石马。再往南是一处独立的宅院,主人系赵氏族人中的护陵人。据说,坟场中的零散土地都由护陵人耕种,所获之物即为赵氏家族提供的“俸禄”。越过石砌牌楼,迎面是座最大的坟冢。两侧稍小些的坟冢前各立一座类似庙宇的碑楼,里边各有一个用乌龟驮起的石碑,碑文清晰可辨。
可惜我们少不经事,虽然相互驮扶着隔门窥望,却并无斩获。老人们说,那个最大的和稍大的坟冢都葬埋着赵家史上最显赫的人物。但究竟官至何级,没有人能说清楚,我们自然也不得而知。但从整个坟冢的规模和气势而言,这个赵家坟一定极有历史了。首次荒冢探秘,我们还是有些害怕,逗留片刻便匆匆返回了。
整个赵家坟内均被高大粗壮的杜梨树所覆盖,早春时节,杜梨花怒放,香飘四溢。金秋十月,杜梨相继成熟,累累果实挂满枝头,煞是好看。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摘下部分果实,味道苦涩实在难以下咽。坟茔间布满奇花异草,间或还有酸枣、狗奶儿等红黑相间的果实,酸甜可口,这才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经常来此玩耍嬉戏的吸引力。
后来,听大人们说,这里还常有狐狸、野兔、獾等野生动物出没,这更增加了我们探幽的兴趣和来此的次数。可惜,这些小精灵没有一次被我们遇见。只有一回,听说有人发现了獾的洞穴,正在组织人开挖,我们赶快跑去观看。忙活了半天,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大人们说,獾很狡猾,很可能是顺着另外一个通道逃走了。
转眼到了1958年,全国上下大炼钢铁,到处搭建起小高炉炼钢炼铁。赵家坟成片的杜梨树竟也难逃厄运,成了釜底之薪,原本浓荫密布的坟场瞬间便变成了光秃秃的坟丘。我们几个小伙伴见到此情此景都难过得哭了,那杜梨的花香、苦涩的果实再也闻不到看不见了,那甘甜的酸枣、狗奶儿也无处寻觅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赵家坟。各类运动接踵而至,赵家坟的命运可想而知!那石砌的牌楼、石人石马都早已不知去向。据说,护陵的人家也已绝户了。如今的坟场旧址上建起了高楼,已经是喧哗的市井。
曾想,如果赵家坟还在,能否开辟为一个旅游景点,或许还能有考古或其它历史价值。对我而言,比起那些乏味的人造景观,那里至少曾寄托过我们欢快的童趣。